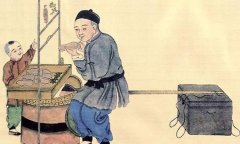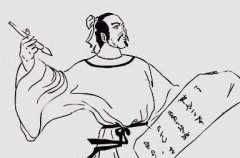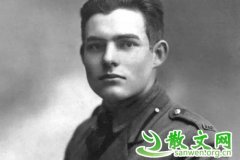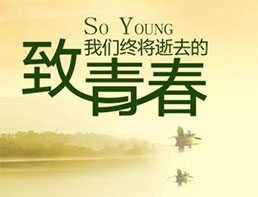外公
2019-01-18 10:39 来源:散文网
外公去世快要整三年了。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在亲人过世整三年后,要再次设宴款待至爱亲朋,乡亲好友,在坟前给他竖碑立传,为亲人祈福。在这样的日子里,自然而然我又想起了外公。外公生前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恍若就在眼前萦绕,不由人眼眶盈热,鼻头儿酸酸,泪流一把......
外公的一生,命运坎坷波折,享过福中福,吃过苦中苦,当过阔少爷,做过小乞丐,尝遍了人生五味,也看尽了人间冷暖。外公身材瘦小单薄,却心胸豁达开朗,风趣幽默,再苦的日子他依然能够黄连树下弹琵琶,讲个笑话,吼句秦腔,苦中找点乐。
外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外公原本是甘肃徽县的一名药材商,也曾富甲一方,显赫一时。家里住着宽大的庭院豪宅,街市上经营着红火旺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家里丫鬟、仆人、店员、伙计雇了六七十人。外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个小少爷。外公的母亲去世的很早,他对母亲没有任何的印象。虽然失去了母亲,但身边总有奶娘和丫鬟细心周到的服侍,外公倒没觉得母爱的缺失,像所有小男孩一样活波开朗,健康的成长。(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从小失去母亲的外公被众人娇惯和宠溺着,他无忧无虑,任性顽皮,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调皮捣蛋气先生,就是不好好念书习字,丫鬟奶娘成天紧追在他屁股后面喊“小少爷,你慢点。”外公却越跑越欢,逗着她们玩。外公最头痛的就是每天傍晚太外公回家检查他课业的时候,每每此时他倒是乖乖的低眉垂首,任凭太外公训斥一番,但从不改正。对于这个顽皮的小儿,太外公也拿他没招,打他吧,他实在是长得太瘦小,又可怜他没有亲娘,不忍心下手,只能无奈的叹息一声:“唉,小冤家。”好在外公还有个哥哥,也就是我的大爷爷。大爷爷从小就懂事,勤奋好学,处事稳重,小小年纪跟着太外公学做生意,研究药材,并对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太外公因势利导,送大爷爷去跟了一个有名的中医先生学习中医。将来的家业和生意太外公也指望着交给大爷爷来打理了,至于外公,也只能让他由着性子做个无忧无虑,一辈子不操心的悠闲阔少爷了。
世事多变化,人生太无常。外公十三岁那年,风云突变,太外公跟人合伙做生意,一夜之间赔了生意,欠下巨额的债务,合伙人逃了个无影无踪。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太外公上当受骗赔了生意的事情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徽县县城的大家小巷,男女老幼,那些与太外公常年合作的客户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互相转告。很快,讨债的人挤满了铺子和家里。太外公为了偿还债务,变卖了商铺、房子、院子,遣散了家里的丫鬟仆人们,带着外公和当时还是丫鬟身份的外婆离开了徽县这个让他伤心难过、并令他感到蒙羞和受到耻辱的地方。太外公就此离开徽县,至死都没再回去过,甘肃徽县成了他老人家的心头之痛。大爷爷因为已经成家,未跟随太外公一起离开,而是跟随妻子去了岳父家里,寄人篱下。外公的小少爷生活就此结束了。
从甘肃到陕西流浪的日子,让外公吃尽了苦头,也看尽了世人的冷眼。从一个富家少爷到一个乞讨的小乞丐,中间没有任何过渡,他的生活一下子从天堂跌倒了地狱。一路上外公是叫苦不迭,受不了苦,咽不下饭。粗糙的饭菜他如同嚼蜡难以下咽,却只见太外公依然一脸平淡,语气平和的对他说:“孩子啊,人到这世上走一遭不容易,什么样的日子都要经受的住才行啊!”慢慢地外公习惯了,恍如一夕之间长大懂事了一般,不再言苦,不再喊累,反倒学会了照顾太外公和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的外婆。渴了,累了,总不忘先问太外公一声:“爸,要不要歇歇?要不要喝点水?”
外公实在是个有福之人,有个不离不弃忠心耿耿的外婆跟在身旁,一辈子外婆既拿他当爱人爱着,又拿他当少爷般呵护照顾着。小外公几岁的外婆不论是干活还是处理事情总表现的比外公成熟稳当很多,再加上个头比外公高一大截,外公就“大姐”“老姐”的叫了外婆一辈子。外婆从小被继母虐待,在家是非打即骂,后来被继母卖到太外公府上当了一名使唤丫头。太外公遣散家人的时候外婆死活不愿意再回到她那个令她胆寒心怯的家,宁愿跟着外公父子一起流浪,再苦的日子她也愿意。
初到陕西,身无分文,人地两生,受到了村里人的排挤和欺凌。太外公给村长好话说尽,冷眼看遍,才央求村长答应他们在村子最边远的一个小院暂居,自己动手,一天时间用树枝搭起的简易房屋,一家三口总算是有了一个容身之地。
外公外婆长大后,太外公做主给他们成了亲。婚后他们接连生下了七个孩子,加上太外公,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在了身高不足一米五五,身单力薄的外公身上。为了养活养活一大家子人,外公给人当过长工,锄草种地扛过活。后来省吃俭用省钱买下了一头牛。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他的牛伙计在山沟沟里给人犁地、耕种,或者为来往的车辆拉拉坡,辛苦一天下来就赚几条或黑或黄的馒头带回家。傍晚时分一身疲惫的外公回家看到的总是孩子们望眼欲穿的眼睛,眼巴巴就盼着他回来带着馒头填饱肚子。带回家的馒头外婆接过去分成几等份,一人一份,不偏不倚。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急不可耐的馋相将馒头吞下肚,外公外婆不忍心再看,偷偷躲出去流一把眼泪儿。每一天外婆总照例偷偷的藏一块馒头留给外公第二天一大早带走,让他路上好充饥。在那个饥荒的常有人饿死的年代,外公用这个办法让一家老小平安地活了下来,实在是个奇迹了。
那头老黄牛最后成了外公最好的伙伴,吃饭的时候外公习惯性的端上饭碗圪蹴在牛槽前看着他的老伙计吃草料,常常会感慨的对他说一句:“老哥哥,辛苦你了。”这头牛最后病老的时候外公伤心难过了好一阵子,他阻止对它宰杀,将它埋在自己经常耕种的田地头,并为他的老伙计修了一个坟头。干活累了,他就蹲在牛坟前歇会儿,絮絮叨叨陪着他的老伙计说说话,好像它还活着一样。
外公一辈子对饮食很讲究,不暴饮暴食,不抽烟,唯一的爱好就是喝两口小酒儿,但他从不贪杯,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后喝一小杯,晚上睡前再喝一小杯。他这样喝酒有什么讲究还是作用我不得而知,只记得他的酒瓶子里总泡着东西,红红的枸杞、人参、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药材。小的时候很好奇外公为什么每次喝酒都会美滋滋的“滋”一口喝尽,闭目仰头很享受的样子,以为那是世间最好的东西,于是央求外公也要喝点。外公呵呵笑笑给我和姐姐都倒了点,小心翼翼伸出舌尖浅尝一口:“呀,咋这么苦辣?难喝死了!”呲牙裂嘴被呛出眼泪的样子逗笑了外公,从此不再惦念外公的酒瓶。
外公少时不好好学习,但他识字,偶有闲暇会拿起书本阅读。外公看得最多的并不是太外公留下的医书,而是菜谱。他喜欢研究做菜,普普通通的大白萝卜外公可以变着花样做出几十种不同的菜。外公做菜既麻利又好吃,舅舅们曾取笑外公:“作为一个农民,你这就是有点不务正业哈。”后来村里有人过个红白事,过来招呼一声,外公就会带上他的厨刀砍刀等一应工具热心的去为他们做厨。每一家过事都需要起早贪黑忙碌两天,外公毫无怨言,反倒很享受的样子。两天下来,回来时主家总会答谢外公一两斤的方子肉,外加一条廉价的被面或者毛巾。外公并不计较报酬的多少,只关心他菜品做得是否可口。外公年龄大了以后,舅舅们不愿意他再如此辛苦,阻止他再去做厨,但他不听,哪怕到现场去指导都可以。
外公外婆年轻的时候吵没吵过架我不知道,在我能记事起没听他们吵过。外公爱开玩笑,进门搁下锄头就是满院子找外婆:“老嫂子,我回来了。”他管外婆从不叫名字,不是“老姐姐”,就是“老嫂子”,所以我一直以为外婆要比外公大,细问才知道外公大几岁。外公的胡乱称呼外婆从不计较,他叫什么都答应。劳作了一天的外公晚上围在火炉旁,悠闲地熬点红砖茶,金亮的汤汁,浓香的茶味,给自己倒一杯,不忘了给外婆也倒一杯:“老姐姐,过来歇歇,喝点茶。”两位老人围着火炉细品茶香,聊着家常的情景是我印象中最温馨的画面。外公的下午茶有时候我们也能跟着沾点光,就着茶香,再吃两颗外婆特制的酒醉酸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的回味。
外公一辈子做的最明智的事情就是不论生活再苦再难,咬牙坚持让孩子们读书学习,或许他从自己小时候没好好学习中有所悔悟吧?寄希望于孩子们身上。外公在其他事情上都很娇惯孩子,唯独学习和教育上他要求非常严格,也有一把当年太外公训他的戒尺拿在手里威慑和吓唬孩子。那把戒尺我挨过两次,第一次见外公生气发脾气吓坏了我,那次好像是因为我把课本撕下来叠了纸飞机,被外公在屁股上狠狠地揍了十下,疼得我“吱哩哇啦”乱喊叫,外公不许外婆过来护着:“我看你记不记得住教训,小小年纪就不好好学,连课本都撕了,无法无天了还。”被外公一番训揍后我是乖了很多,书和本子都特别的珍惜起来了。外公一天到晚不离口的家训就是:“为人首先要诚实,讲诚信,要孝顺。这几点做到了,不论穷日子还是富日子,安然自在的过,都是一个活神仙。”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舅舅姨姨们在如此贫穷的家庭长大,对学习都非常珍惜和刻苦,尤其是两个舅舅,大舅舅大学毕业,小舅舅研究生毕业,这让从没出过大学生的小村庄一下子沸腾了。看子敬父,舅舅的出色让外公在村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大舅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大型煤矿的矿长以后,外公在村民的口中称呼就成了“老太爷子”了。
渐渐步入老年的外公对身体的保养和锻炼非常重视。我能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外婆家,每天天不亮就会被外公拍打屁股叫起床,我、姐姐和表妹三个娃娃迷迷糊糊中跟着外公出门跑步。出门就是西沟,外公先带我们顺着小路跑到沟底再爬坡返回,上来在碾麦子的场子里外公一招一式教我们几个打太极拳,太极剑。一把木头削成的木剑,外公还硬问外婆要了块红绸子绑在剑柄上,看起来有点像模像样。为了我们几个小孙孙能够跟着他好好锻炼,他又为我们几个做了几柄小木剑,同样的绑上了几块红绸子。外婆呵呵笑笑,由着我们爷孙几个折腾。
外公的另一大爱好就是拉二胡唱秦腔,那吱吱呀呀的曲子我是听不出个好赖,但是外公闭着眼睛摇头晃脑的拉得很陶醉。听外婆讲,在那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年月里外公也没丢过那把二胡,时不时的拿出来拉上一段给她和孩子们听,在那一刻他们忘记了所有的忧愁与烦恼。外公老年的时候,舅舅、母亲和姨母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他们就给外公买了很多的秦腔磁带、碟片和剧本。那些磁带和碟片外公走到哪带到哪,孩子似得不许我们动他的宝贝。在外公去世后,舅舅将他的那把二胡、木头宝剑和那些磁带碟片一起给他放到了坟墓里。
外公的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但他传承了太外公的秉性,高兴不过喜,痛苦不过悲,清心寡欲,世事看得开,想得淡。八十六岁无疾而终,面带笑容,走得非常安详......
本文由散文网用户整理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