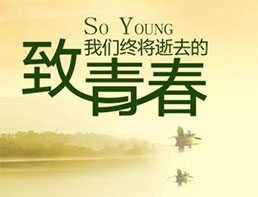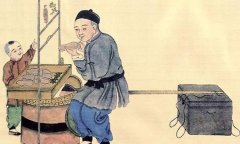还原的文章
2019-01-15 12:03 来源:散文网
篇一:还原
学化学的时候,有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其实,生活中经常离不开这两种反应,当外界条件变化的时候,就会出现氧化反应,使物质发生质的变化,当变化的条件拆除之后,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即还原成本来的生活状态。
上课或考试本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老师在台上悉心教导,学生在台下认真听讲,或者学生在紧张做题(表演节目),老师(评委)在认真监督、仔细观察,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师生关系一定是纯真的、没有水分的。
可是,当周围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任何学历和资格,任何水平和荣誉,都能由金钱来操控的时候,师生及其他社会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老师也许是骗子,学生也许是恶霸。互相欺骗、不讲信用,横蛮无理、唯我独尊的人际关系,就会扰乱社会秩序,使人与人之间就像衣服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需要用力拍打,用强去污剂洗刷,才能干净,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虽然不再是崭新的衣服,但是,干净的总比肮脏的要好,尽管它不显眼,就是贴身的、暖和的。
当一新鲜事物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人们总是好奇的、热情的。当此事物反反复复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厌烦、逃避了。假如我们是此事物中的一份子,请千万不要害怕失去周围人的关注,因为人的一生中,上台表演的机会不多,有人拍掌鼓励过就很不错了,不要期望他人一直为你鼓掌下去,这样既伤害了他人——没有休息的余地,搞得身心疲惫;也伤害了自己——始终站在台上表演,哪有时间调节生活,给大家一个惊喜呢?
学会还原自己,让自己不再为了“表演”而耗尽心血,同时,也让他人还原,不再牵挂你而耽误时间,影响情绪和生活。也就是说,看电视看电影或看歌舞晚会看各种比赛,只需要少部分时间去参与热闹,无需整天整月整年地守在某个地方,不知道回家。只有家才是温馨的,不管是个人租住的单间,还是结婚成家之后的小家,还有父母、兄弟姐妹在场的大家庭,或者是自己的单位、团体,乃至整个国家民族,都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还原,就是回归自然,回到属于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迷失方向。回家的感觉真好,
篇二:还原
从今天晚上开始,一切又一次还原到以前的样子了。午夜时分,外面的世界更加的静了,蝉们也不叫了,只因为昨天的那场雨。很大,很大。被雨水冲刷的街道明快了很多,道边只剩下被雨水带动的灰尘的堆积。片片连连。
老友在我这住了将近有半月的时间,临走时,我说,你算是熬出来了,两口子又能天天见面了,可是美了你了。友,笑而不答。
他走后,我还是依然窝在沙发里。松松软软的感觉。电视上播放着游泳的比赛,双臂挥动溅起了水花,努力的向前游着。
电脑中老友玩儿游戏的通关记录很高,但我是没有兴趣的,因为我不把时间花到种植花草和味餐厅打扫卫生上的。打开音乐的记录器,还是常听的那几首歌,虽说是来来回回的放着,但依然味道十足的,不亚于餐厅中厨师的绝品美味。旋律回荡在四周,盎然之间,让我心醉了,只因为它们值得我去品读的。(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擦擦地,露出了光色。也许它们也在期待,期待从尘世中惊醒,从带着远古的浸湿到今生的畅然挥洒,不知道游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历经了古今朝代的变迁,看穿了时间的溜走,附上满身的灰尘,记载了沧桑的过往缓缓睡下了。不在出声了。
屋里的物件最了解我的心情,跳摇着回到原本的地方了,那里才是他们的归属,才是最适合的地方。
烟缸中的灰满了,倒掉,哈拉一声,灰溅起的雾,久久不能散去,记载了时间的脚步,传递着远足的信息。
将屋里的灯全部打开了,通通亮。我坐的光影中,听她的诉求。此时我又看了看墙上的钟表,还是走着了。灯光照在表面,照亮了三兄弟前行的路,如灯塔在远方,漂浮在海面了。
我还是拥有着岁月的清爽,捧上一本书,哪怕是短短的时间,翻阅着被错过的缘分。也许就在字里行间中,能有醉花生香了,为我这个陋室,点缀了一缕淡淡的甜和悠然的酸。
篇三:还原的店名
顺着当年慈禧老佛爷西行的道路走,出京不远就到了这个塞外小城。
四四方方一座城,可能当年建城伊始都是这个样子。据康熙年间编纂的县志记载:“这座小城,明景泰二年筑,{公元一四五一年筑}隆庆三年砖修{一五六九年}垛口砖砌,墙灰沙砌成,周围二里四十二步,高两丈九尺,厚六尺五寸,东西街长一里五十一步,共三堡,东二堡相连,西另为一堡。中有老龙潭,水出其间,堡人建石桥一洞,中堡有关庙。”
就是这么一座小城,五百多年的斗转星移,恍惚间变了摸样。一条街道长的都望不到头,高楼林立,霓虹闪烁,俨然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现在找寻小城的遗迹,真的还有一个城门洞在沧桑中耸立着。保存的还不错,一个叫火巷口的小巷穿越其间,窄窄幽幽的街道,闹中取静的民居,倒是添了几分古色古香。
这个小城历来不缺少商贾店铺,老县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修水库被淹了,从此这个小城就成了县府的所在地。
解放初期的时候,这里的商业还算繁华,一般的日用百货都能买得到。况且这里是东临京津,西连内蒙的交通要道,商潮流动,商贾穿流,街上的店铺更是鳞次栉比。
老周,子承父业在这条街上开了一间剃头房,门脸不大,放得下三四张椅子,名字也不够响亮,就叫周记理发店。
他耍的一手儿好手艺,理发,剃头,刮脸,按摩推拿,样样精通,推子,刀子,剪子,篦子,抄子,工具样样齐全,就连当时女人的火烫卷花,都略知一二。在当时,能有一间临街店铺,不受风耗雨洒,日见现钱,小日子过得绝对够滋润。
这条街道上,除了理发的,还有酒馆,饭铺,旅店,澡堂,照相,杂货铺,米面铺,笼箩铺,度量衡,{卖称的}熟皮子铺,百货日杂店,琳琅满目。要是逢个赶集上店的节气,满街筒子都是人,熙熙攘攘,拥来挤去。这时候,老周的买卖格外的好,刀子刷刷,剪子咔咔,黑的,白的,花白的头发,半天的功夫就积起一地。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公私合营了。凡是与服务业有关的,都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机构——饮食服务处。房子归了处里,工具随人走,每个人给了一张入股的发票,这就成了公家人了。理发的店铺也收编了不少,为了区别差异,什么东堡理发馆,顺城街理发馆,还有理发社。
散落的理发“铺,”被串在一起,升格为理发“馆”了。
日子就这样过着,木椅子变成了铁椅子,手推子变成了电推子,有了电吹风,有了化学烫,有了染发制剂。但是,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手艺好坏一个样,出工不出力,有病大养,无病呻吟,熬年头,混工资。老周的头发已经显出了几丝白发,无奈里透着无奈。
史无前例的运动来了。走出店门,上山下乡为工农兵服务,到乡下点种抗旱,挖地道备战备荒,都成了工作的内容。就连店名也变了,卫星理发馆,红卫理发馆,工农兵理发馆,取代了东堡,西堡理发馆的名称,玻璃上都印上了放光的红太阳。
事情终于结束了。又回归到刀子剪子的声音里来,理发馆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空气里还是那样,弥漫着肥皂水和来苏水的味道,只是老周的白头发更多了,老周有些老了。
事情发展到下班后可以“干私活”了。老周基于家庭的困难,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租了一间门脸儿带着儿子开始干自己的事儿了。手艺好,人不请自来。老周下班后的买卖很火,干的也越来越起劲儿,儿子的手艺也是日渐提高。老周终于熬到退休了。他明目张胆的以儿子的名义领了营业执照,一个时髦的“秀丽美发屋”焕然一新的开张了。
老周还是老周,只不过增加了儿子小周。起名字的时候,儿子坚持这样叫,老周有些反对,但还是妥协了。后来,凡是来的老顾客都觉得反感,觉得不是味儿,建议老周换个名字,老周倒是重视了,儿子还不以为然。毕竟顾客是上帝,说的人多了,不得不上心。
老周与小周可劲的琢磨,发廊啊,美发厅啊,理发馆啊,造型屋呀,都不适合,最后老周一锤定音,还叫“周记理发店”。这下好了,来的顾客都喜欢这个名字,说来也是,老周小周仰仗的就是城里的老顾客,价钱低,手艺好,就连名字都经济实惠。
这个名字追根溯源是老周的老周起的,真的,这个名字名符其实,挺好。就这样,周记理发店还在小城的城墙角下开着,直到现在。
本文由散文网用户整理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相关阅读
-

这,就是幸福
幸福美好,这是多么诱人的字眼,这是多么令人神往和追求的完美境界! 然而,幸福,没有确切的定义,一般是指人们无忧无虑、随心所欲地体验自己理想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时,获得满足的心理感受...
2020-11-28
-

有一种目光,一直在守望
一份真挚情谊,不求时时相伴,只求在心的牵念中永远,相互尊重,相互分担,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这种真情,值得用生命去呵护,用灵魂去写真,生命中,总有一首歌曲,沁入心灵;总有一种眷恋,默...
2020-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