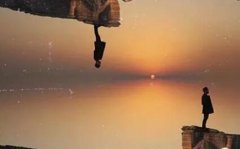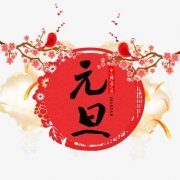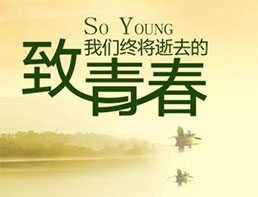关于风的文章
2019-04-09 22:05 来源:散文网
篇一:微弱的冷风
终于挤进了候车厅,轩稍微缓了口气。
可是,眼前这片汪洋人海,让他又觉得很不自在。放眼四周,连个座位都没有,又是大热天,这么傻站着累不死也热死了。他拿起行李,开始找寻位子。
刚好,有一行人都起身向检票口蜂拥而去。他瞅准一个,一屁一股坐下去,这才松了口气。放下一身后的背包,站起身,擦了擦额头的汗,用手抖了抖已经贴在身上的T恤,心中直抱怨。候车亭这么多人,又是大热天,怎能不开空调呢。
离上车还有一段时间,他只好拿出手机玩,打发时间。
也不知道啥时候,他正玩的起劲,忽然听到附近有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念道,谢谢了,谢谢了。他没在意,继续玩着,一会儿声音更近了,猛地一抬头,眼前一个穿着朴素的女人已把方便面桶伸到自己面前,里面满是一一毛一,五一毛一,一块的零钱。女人一直弓着腰,另一只手还拉着个4岁左右的孩子,一只手拿个小面包,不停的用嘴撕咬着。
他知道意思了。没太多想,拿出钱包取出一块钱,轻轻地放在里面,冲那个女人点了点头。女人往旁边挪了一步,继续向旅客乞讨。轩正要回头继续玩手机,眼前突然又伸过一只手,抬头一看,是旁边穿白色裙子的阿姨,手拿一张五元钱,急忙把钱递给了那个女人。然而,身后却传来了斩钉截铁的声音,没有。女人沉默着,转身走了。
这时,这个声音又继续道:“这个女人前些天就在这了,竟然还在这!候车厅没有票怎么可能进来。大家可要注意,别被骗了,不然就“杯具”了!轩随着声音回头一瞧,两个中年妇女坐在一块,胖点的大妈看他回头,就笑了笑,好心的说道:“小伙子,是真的。”没等轩回话,瘦点的大妈也劝道:“留给心,总没错。”轩看了看孩子,;脸上显示出不相信的表情。
“电视上不是都报道了吗?有的青年都骗人,不知在哪找的‘妈’,他‘妈’躺在旁边,他不停的磕头,不一会就进账一大笔;还有人以这个为职业,竟然用乞讨来的钱盖了三座洋楼,一栋别墅,两辆名车!”胖大妈察觉到轩似乎不信,急忙热心的补充道。
不过,瘦大妈却盯着那个女人和孩子,仿佛要帮大家看穿面前的乞讨者。可是,看到那个不经世事的孩子,她愣住了······
女人已经转身到对面去乞讨了,依然弓着腰。不过刚才那些话却对这些人产生了作用。第一个大姐爱理不理,头扭到一边去。女人又向旁边的年轻妇人递过去方便面桶,妇人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女人看。然后看看旁边和小孩玩耍的男人,男的好像不太高兴,也许嫌弃女人打扰了他和女儿的雅兴,拿出五一毛一钱,扔在里边,用手示意女人赶快走开。旁边这位大爷谨慎地拉了拉包,把一块钱轻轻放在桶里,没有言语。
紧挨着的那个穿着时髦的男人抱一紧了挎包,任凭女人怎么哀求,也没有动静;挨着的帅男孩佯装在睡觉;旁边这个戴着金项链的男人像看笑话一样看着女人,没有动静。女人刚要再向别人乞讨,小孩拉了拉她的手,举起一直抓在手里的小面包。女人似乎明白了,拿过面包,用嘴撕一开,放回孩子的手里,又开始了乞讨。
“前两天不是给你买票了吗?那个大叔给你们给了钱,买了票,你们怎么还在这?”听到声音,大家都把目光投到那个女人身上。只见一个穿制一服的工作人员疑惑地看着女人。
“我说对了吧,分明是骗子,你们还不相信。”胖大妈神奇而又悻悻地说道,好像认为自己就是神。
那个女人有点不好意思,脸通红,依然弓着腰。嘴里念道了几句,轩终于听清楚了,钱和票又丢一了。看到眼前这幕,那个工作人员叹了口气,怜惜的拉过孩子的手,说了句:“我给你们买票去。”然后,扶起弓着腰的女人,轻轻拍了拍女人的背,让她直起腰,走了。
胖大妈低头扯起了衣角,瘦大妈却一抽一泣的说道:“我第二年回娘家,也遇到同样的事······
虽然已是盛夏,轩却感到了高温酷暑中的一丝凉意。那股微弱的萦绕在大厅的冷风依然能浇灭人们心头难以忍受的热火。
篇二:洒脱的风
风在蒙自是有极高的知名度的。
在我准备调到蒙自工作之前,有人就曾劝我三思,其中的一条理由是蒙自有“三恶”,即:风恶;蚊子恶;老母猪恶。风还在“三恶”之首哩。
这是一则民间笑话,它用嬉戏的方式,说明地方的一些自然风貌,说出了风在蒙自的突出特点。而最后面一句,也许旧时存在过,或许是出于一种顺口溜的需要,为了补充、点缀前两句而编撰的。
早几年,我倒是真的领略过一次蒙自风的威力。
大概是2001年的春季吧,妻子利用寒假在蒙自师专攻读大专文凭。那次我到昆明开会,回来的时候顺便拐进蒙自,来看望妻子。回屏边的车子直接把我送到了师专门口。进了师专大门后,我在院子里一边随意走动游览,一边等妻子出来。风就从前面呼一呼地跑来推我,仿佛它代表学院,不欢迎我的不速造访,毫不客气地要把我推出门外。那些高大的棕榈树也借助风的威力,哗哗哗不停地拍打着伸展的叶掌,虚张声势。
那股春风,真有一种不摆不休的气势。
之前,我就听妻子说过蒙自风大的话,不以为然。直到这次自己亲自感受后,才觉得真的名不虚传。
风的“恶名”最终并未能阻止我走向蒙自的脚步。2007年年末,一纸红头文件,让我成为蒙自一名合法的居住者。
我住的红河富康园小区的大门头上,住户正式入住时,物管处为了营造喜庆气氛,同时表达对新的住户的祝贺,插了一些彩旗。现在,那些彩旗大多只剩下杆杆了,有几条没有被风撕扯干净的布成了彩条后,也一刻不得息,依然被风不分早晚地拉扯着,成天呼一呼飘摇。它一直让我感受着初来乍到时的那种欢快和喜悦。
我家客厅的落地窗开朝南面,平时,总有一扇玻璃窗开着,只关纱窗。有风使劲从纱窗挤进来,在屋里兜一圈后,又想溜出去。但退出去比进来就更难了,风大一点的时候,在内外风力的相互推挪下,上半截的窗扇就会不停地有节奏地“咚咚“摇动,仿佛有个孩子被关在外面不时地过来,调皮地叩着门窗,令你一刻也忙不得寂寞。
春日的一个中午,饭后我在县行政中心大楼前慢步,台阶上和台阶前,摆着一盆盆的菊花,开满了小巧而黄|色的花朵。风好像在寻找什么,极具耐心地把那些小小的花一瓣翻来翻去。风一直不断,花一瓣的翻一动也一刻不停。我看了半天,却没见一片花一瓣被撕掉。那一刻,我明白,风也会怜香惜玉啊!(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夏天的某个夜晚,我在陽台上听蛙鸣。月明风清,风在天上抓着一把白云,一一夜不知疲倦地轻轻擦一拭着月亮的面庞,使月亮始终保持着皎洁的面容;天空也一派清明、空旷。风也在地上不停地游荡,这里看看,那里走走,亲一口这棵草,抱一下那棵树,也不时忘情地搂搂我。那一刻,我知道,风还通人性哩!
现在的夏季,很难找到一个清凉的地方了。夏天,我不想到一些地方出差,因为不但气温高,连风也是热的,吹到身上,让人热上加热,一天到晚叫人浑身汗腻腻的,风再大的冷漠也不足以降低酷暑的高温。无疑,蒙自的夏天也是热的,但在蒙自不会出现那种醒暑难当和闷重不堪的感觉,除非你本身就闷在不通气不通风的环境里。一句话,在蒙自过夏,是不需要借助空调的。在室内,只要开窗,有风自然给你送爽;在室外,点点树影就让你得到凉快。同样,本应炎热的蒙自夏夜,因为风的加入,变得清凉、舒一爽;有时站在外面的时间长了,甚至于会有点淡淡的寒意。这都有得于蒙自的风,蒙自的夏风成了蒙自气温的调节师,它潇洒地掌控着天地赋予的特权,却极其公正。它把无边的酷暑带走,还给你一个清凉的世界。
这让我觉得,蒙自的风是有魔力的。而有魔力的东西,往往是独特的、别具的。
每天,风在黎明之前,就轻轻地唤醒了蒙自,唤醒了我们深沉的睡眠。牵着风的衣襟,我们每天在生活的身上行走,缓缓或者匆匆都由不得自己,我们不过是时间的过客,风的过客。风像生活的影子,在我们的双脚间蹿动,加速日子的步伐。
更主要的是,风永远走在人的前面。风是大自然送给这块大地的一宠一儿,风是太陽派驻地球的使者。风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在这个叫蒙自的地方安居乐业了。祖先只是跟在风的屁一股后面,在若干百年前或者若干千年前或者若干万年前,突然发觉这是个好吃好在好劳动的地方,就小心翼翼地在风的手掌下住下,企求与风为邻,在这个地方享受美好生活。
拐弯抹角或者跳上蹿下什么的,对风来说不过小菜一碟,一点难不住它。但估计耿直的风肯定更喜欢平铺直叙直来直往。一马平川的蒙自,正合风的心意。
这里的房子也不高,普遍四、五层楼的高度,需要翻越时也毫不费吹灰之力。风也就懒得管人的闲事,想躺就躺,想跑就跑,继续在这里横冲直闯,来去自如。
还有那满街满地的绿化带,得到丰厚的陽光的爱抚,矮的草,高的树,都长得一块块一片片碧绿碧绿的,那是风一生追崇的色彩,风丢不开对树的迷恋,对草坪的热爱。风就成天在树枝上跳舞,在草坪上打滚。
并且,风也和人一样,也是有懒惰心理的。在遍布崇山峻岭的滇南,难得出现这么宽阔的一块坝子,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已经早就生活惯了自一由惯了,风才不会轻易拱手让给人类,自觉退出这方宝地去别处浪迹呢。
篇三:风玲
在相恋六年后,风终于要和玲结婚了,这无疑是当中最的时刻,结婚的前两天,风对玲说:要去商场里给她买一件裙子,玲说不要去了,外边天这么热,等过些日子再买也不迟。风坚持要去,玲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风在商场里转了半天,终于选择了一件紫色*的裙子,在回家的路上,他不停的看着手中的裙子,想象着玲看到裙子时的开心笑容,但风却忘记了看周围来往的车辆,正当他抬起头注意前方时,一辆汽车从他左边急速经过,风还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被车撞的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十几米开外的地方,他的后脑在不停的流血,司机下车看了一眼,留下一句活该,疾驰而去。而风的手中,还紧紧一握着那件紫色*裙子。
当玲来到医院时,她怎么也不敢眼前的一幕:风静静躺在停一尸一间,面无表情,玲用力捶打他的胸口,疯了一样叫他的名字,可风没有一点反应,他离开了,永远离开了。
玲的哭声久久在医院回荡着,当警察把那件紫色*裙子交给玲时,玲静静接过裙子,没有和周围亲属说一句话,悄悄离开了,她的背影看上去很沉重,脸上写满了痛苦两个字。
风火化那天,玲没有去,亲戚们不想让玲再一次痛哭流涕。而玲呢,现在正呆在他们的新房内,望着前些天刚刚拍好的婚纱照,一动不动。此时,房间里静的让人有些害怕,仿佛只能听到玲的呼吸声。突然,玲不知怎么,疯了似的用头磕着墙壁,不一会儿,她的脑门前布满了鲜血,鲜血染红了她的脸庞,也染红了白色*的墙壁,玲此时脸上露出了微笑,而这微笑随着她的倒地,也戛然终止。
不知过了多久,玲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她慢慢起身,此时她的眼前一片红色*。开了门原来是玲的,看到女儿满脸是血,吓坏了,拉着女儿就往医院走,在医院里,医生给玲做了仔细的检查,在确认只是皮外伤时,玲的父母才松了一口气,安慰女儿要想开,不要悲伤。可女儿在听到他们的话时却没有一丝反映,他们仔细观察女儿才发现,女儿的眼神十分迟钝,整个人看上去有些呆滞,他们不知所措,立刻叫来医生,在一番诊断后,医生告诉玲的父母:你的女儿,得了精神病,当听到女儿得的是精神病时,玲的晕倒在地,当她醒来时,玲的对她说:你好些了吗?医生说必须让女儿接受治疗,否则这种病就很难治愈,玲的点点头,表示同意。
此时的玲,坐在病床上傻笑,嘴里还在不停的说着些什么,忽然,她大哭起来,大叫着:风,你在哪,你在哪啊。玲的身体在不停一抽一动,她用水杯打碎了玻璃,然后用玻璃碴割自己的手腕,幸好此时医生及时赶到,制止了她的行为。
以后的日子里,玲经常手握那件紫色*的裙子,唱着旁人听不懂的歌,她让得很投入,一唱就是两三个小时,玲的父母听着女儿的歌声,心都快碎了。
三年后,玲出院了,回到家的她感觉轻松了很多,她不敢想象自己这五年是怎么过来的,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而自己在这场噩梦中一直沉睡了五年。看着憔悴的父母,玲心里难过极了,他们为自己付出了太多,一辈子都在为儿女操心,想到这,玲跪在地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头,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愧疚,而父母看到女儿的举动,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
篇四:风格
装潢公司的设计师喜欢胸有成竹地问顾客:“您要什么风格?”
每逢有人这么发问,我就比较紧张。风格,多么的高雅!用到我身上合适吗?我一个老百姓,有一套不漏风的房子已经不错了,还要什么风格?如果非要说风格,那我的风格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但您还是得要一个风格。”设计师赵先生是个锲而不舍的人,见我眼睛发直,便循循善诱地说:“您来个古希腊的怎么样?再不德国的也成,或者法兰西?意大利?北欧风情?南欧格调?”
我可怜巴巴地说:“我一个土包子,也没去过欧洲啊。”
赵先生笑了:“所以我才建议您弄个欧式的,弄完坐下来一撒目,嘿!整个一个人在欧洲的感觉,飞机票都省下了。缺啥想啥,是咱人类的本性*。农村大炕的布局最省事,给您来一个您干吗?”
赵先生西装革履,精神头挺足,只是袖口油污,气质通俗,也不像去过欧洲的样子。当然,信息时代,大家多是间接获得知识,没吃过肥猪肉,还没见过肥猪跑?他虽不洋气,但天天读一段欧洲的装潢学,也不是没有可能。人不可貌相,那袖口没准就是看书蹭脏的。
见我默默无语,莫衷一是,赵设计师热情不减地说:“这样吧,我先给您出个图,您看合适了咱再装修,不合适我分文不取。”
不久图就出来了,画得挺复杂,又是边圈吊顶,又是壁炉式主题墙,花里胡哨,乱占空间,预算也高得惊人。我挺为难,下意识地一搓一手。赵先生则大度地说:“您不要没关系,王先生要了,我们决定把他家当样板间,将来欢迎您去光临指导。”
没人提一供风格了,只好自己跌跌撞撞往前闯。别想欧洲别想北美,想一想你打算拿屋子干什么,哪一处放床,哪一处放桌子,洗手池多高,你个子多高,把这些想明白比啥都重要。渐渐就弄出现在这么一副格局,虽谈不上时髦,却也舒适实用,挺合自己的口味。朋友来参观,都说你这风格挺好啊,说得我直激动,风格呀风格,我居然也拥有了你。
王先生家也装修完毕。我去了一趟,发现赵设计师在原图基础上又有重大发挥,只见左边是日本的塌塌米,右边是凹凸槽的罗马柱,还有台湾的文化石,街头小饭馆的吧台、老员外后花园的月亮门……主人得意而谦虚地说:“这叫综合式风格,那什么,还凑合吧?”
篇五:风的到来
如果风曾经来过,可曾带走些什么?
十二月的一个夜晚有些平淡,有些无趣。
是今夜了吧,头有些痛,不想看手机,于是有了这篇文章。也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脑袋里面,理科生的思维越来越重,没有从前那般敏感,也就失了太多的,有感而发。
树枝上已经是一片树叶都没有了,可我还有两片,初秋时候捡到的银杏叶,还存着它的金黄,即便是有些憔悴。
每次经过那些树旁,我都会停下来看一看,还能否找到一两片不落的叶子,用来装饰我的墙,可惜很困难。它们总是在该离开时就离开,从来都彻底、干净,到底是雪下过后的季节。我有些后悔,整整一个秋天,却只是捡了两片叶子。
风起了,不再有叶的“哗哗”作响,它们都已去了,树干却还在这,依然那么坚定着,失了叶子,也不怕风了,就这么立着,一直立着,会这样不变的等待着一个季节。
我看见所有的叶子都随风去了,却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从未在天上看见它们的一丝踪影,雨后的彩虹却又和它们毫无关系,云散了,也没有了痕迹,不知道他们过得幸不幸福。是在哪里化成一缕金黄,变成暖暖的光,还是在不知名的角落里老去,枯黄。我只能猜想这一切与风有关系,
我问风,可曾见过一片落叶?
他匆匆经过,脚步里不带任何犹豫,停留。我说,你要去哪里?他以问代答的回复我,去哪里?去哪里……
风说,他从不停留,不会去哪里,不知道去哪里,他会突然消失,时而重现。
“我带不走什么,我曾经试图带着花的芬芳,可走着走着就找不到了。你的落叶也许是我无意带走,不曾记起的丢在何处的东西,然而我却并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追着风,问着许多关于他的经历,有些他也记不清,他说,那些回忆早已忘记,何必又提起?我仿佛闻到了一丝淡淡的花香,他说这是他一直紧握不肯丢掉的,因为那是最美的一次路过,即便不能因此而停留。
“还是会散去的”,我坐在他旁边。
他走了,没有再给我回答。
他还是会再回来的,因为在有一个季节,他可以去再次收集那味道了。
“也许会忘掉吧”。
我把仅有的落叶送给了风,在他经过我的时候。
我松开手,两片写满祝福的叶子被带走,像漂流瓶一样远走,我请风帮我把它送给阳光,谢谢每天清晨她给我的问候。风默许着出发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是谁。
雨后初晴,阳光以彩虹贺我。
我伴着风沉默,看着那道五彩的尽头。
篇六:田野的风
盛夏回到乡下,虽然也很热,但满目是青葱的庄稼,田野的风一阵阵吹来,浑身就感到无比的爽一快。
母亲常说,你住在城里,田野的风都吹不到,夏天虽有空调也不好过。是啊,现在江南一年简直快成了两季,春秋很短,冬夏很长。尤其是夏天,过了“五一”就热起来了,到六月中旬就开始狂一热,一直要延续到八月下旬九月初,燠热才会退去。在城里过夏天,只有成天在屋里孵空调,有时突然停一会儿电,简直没法过。到屋外走在两边都是水泥建筑的街上,犹如进了蒸笼。
有时想想,青少年时在乡下务农,大热天在稻田里拔草,背上大太陽烤着,脚在发烫的水里泡着,那日子是怎么过的?其实,当时也就那样,大家都一样在稻田里干活,热得大汗淋一漓,衣服湿一透贴在身上,虽然觉得很难受,但休息时在树荫下待一会儿,汗湿的衣服被风一吹,倒感到浑身凉爽。那时多么羡慕成天待在商店里的营业员和在屋内工作的人,想象着他们成天晒不到太陽,在屋里摇着扇子或吹着电扇,多么幸福。可现在自己成天待在屋里,冬夏有空调,冷热都不怕,却并不感到有多幸福,人确实是变娇气了。
以前,夏日的晚上,早早地将屋外的晒场扫干净,再洒上井水,然后把方桌抬到晒场上,一家人围着方桌吃晚饭,吃的虽然是最简单的饭菜,茶淘饭就酱瓜,最多有个炒螺蛳,但也其乐融融。晚饭后擦干净方桌,再摘下家里的几块门板,搁在长凳上,小孩睡在方桌上,大人睡在门板上乘凉。母亲和祖母怕我们小孩掉下方桌,就坐在桌边的长凳上,一边为我们打扇赶蚊子,一边指着天上的星星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几家邻居都在一起乘凉,大人们则交流着白天碰到的各种稀奇事。我家晒场前面的田里,夏天常种薄荷,一阵阵风从薄荷田里吹来,特别清凉。再看那些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像提着灯笼的小孩在田里忽高忽低地追逐玩耍。几个小孩终于耐不住寂寞,结伴去薄荷田里捉萤火虫,装在小瓶里当手电,再放到蚊帐里看着玩。或到屋后的竹林里抓纺织娘,放在用麦桔秆自编的小笼里,插上一串一毛一豆或豇豆喂它,挂在房梁的铁钩上听它“织织织织”地鸣叫……
我从15岁离家到外地上学,后来参军到了北方,再后来转业回乡到城里工作,再也体会不到夏夜乘凉的乐趣,也基本吹不到田野的风了。直到退休后我乡下又有了新居,经常回乡下,才又能吹到田野的风。
现在农民新村的住宅条件好了,屋内既有电扇又有空调。夏日的晚上可以在屋内开着空调看电视,但我还是喜欢到屋外乘凉,搬张藤椅坐在三楼陽台,能望见四周不远处长满庄稼的田野。田野清凉的风一阵阵从身边吹来,吹动了身上的衣衫,感到分外舒畅。听着东南面小河边树上知了的欢快合唱,看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从树梢上一点点升起,湛蓝的天幕上数不清的银星在闪烁,间或有几颗橙红的星星在游一动,那是南来北往的飞机,尾翼上闪烁的灯光,多像夏夜田野里游一动的萤火虫。只是,如今农民新村各家都有独立的院子,夏夜邻居不会常在一起交流了。年迈的母亲已上不动三楼和我一起乘凉,妻子刚去大城市的女儿家,全家只有我,在夏夜独享田野的风……
本文由散文网用户整理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