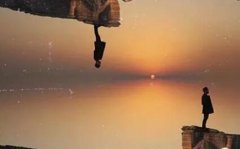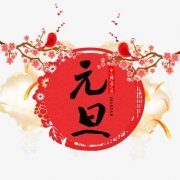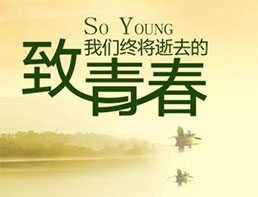关于情结的文章
2019-04-09 22:05 来源:散文网
篇一:小径情结
与小径的相识是在一个没有美丽只有忧伤的春天,那个春天斑斓的不是绚丽和灿烂的光芒,而是沧桑和忧郁的色彩。
或许是他的性情太倔强,不经意间触犯了上司,头儿的一句话就把他“发配”到一个偏远得连鸟都不愿意呆的山区了。这对他来说真的是一种侮辱和蹂躏,背后人们针刺的目光,眼前亲朋鄙视的责备,使他喘息窒息。但是他又不愿委屈自己清高的灵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竭力维护着自己的那点尊严,依然决然头也不会地背起行囊,走向了隐含着屈辱和愤懑的征途。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一直在低沉中消落,回想起工作,家庭,生活林林总总的事情,他简直焦头烂额,痛不欲生。人总是在失意的时候才感觉到人生的艰难和沉重。当他躺在那简陋而破旧的办公室兼宿舍的小石屋中,对着窗外的月光发呆时,他的心情便布满了恐惧和沮丧,他感觉不到人生的美好,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浮躁狂暴、焦虑不安,他感觉他不能再承受任何一点苦难了。
那段时间,他的意志在一点点地消沉,他的神经在一天天地麻木,他要彻底崩溃了。于是,在一个极度消沉的傍晚,他一个人忧郁地走进了那一片朦胧着炊烟和雾霭的山谷,走进了那条从无人问津的在孤独中落寞的小径,然而没想到就是在那时他竟然喜欢上了小径,而且从此他便有了一个孤独的伙伴,与他共愁,与他同欢。
小径蜿蜒在一片低矮的山丘间,孤寂地在山腰间穿行盘桓。以前这里是山里人家通往山外的便道,后来有了大道后就无人再踏了,小径慢慢地就被人们遗忘了。那曲曲折折的路面上铺着被雨水和脚步磨砺的发白的碎石子,那石子干干净净的大小不一,镶嵌在黑黄的但是并没有尘屑飞扬的泥土里,安详而宁静。
小径的左侧是一条悬挂在绝壁的用青色石块砌成的和小路走向一致的沟渠,沟渠里苟延残喘着残弱的让人爱怜的一线从山岩里渗出来的溪水。两边丛生着高高低低的荆棘藤蔓,隔不远处零星地站立着一株或两株桃树或杏树,还有苍老而枝干遒劲的柿树。沟渠下面是一片比较开阔的长长的林带,种满了笔直而挺立的胡杨。小径的右侧是一片低漫的山谷,上面长满了高低错落的密密麻麻的有了年代的苍松翠柏。松柏下面铺积着厚厚的黄中微白的零落的松针柏叶,踏上去软乎乎的很有弹性。还有一些天然的花草和藤条也芊芊莽莽地夹杂在其间,看上去很和谐而充实。
那天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这空空的林谷小径中,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从林梢深处传来几声野鸡的叫声,给这空空的林间增添了一些恐怖的气氛。但是,他却没有感到丝毫的害怕,因为对他来说,一切都失去了感觉,他就那样忧郁地踯躅着,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直到月上山巅。(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那月光静静地把一束束银色的光华抛洒在这片山林间,幽黑的林木映衬着泛着白光的小径,陪衬着一个可以说近乎麻木而神经的他。他在小径上忽而狂跑乱舞,忽而大笑发怔,忽而仰天长啸,忽而哀伤低咽,忽而悲声唳吼。他不知道他是谁了,他傻了,他疯了,他在这孤寂的山林,在这孤寂的小径像洪水猛兽一样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发泄着自己淤积在心底的再也无法压抑的沉闷和痛苦。
没有任何东西理睬他,那松柏,那丛草,那星星,那山丘都好象一个个冷漠的看客,没有什么来抚摩他,安慰他,只有脚下一条无语孤独的小径在支撑着一个痴狂的他,他好可怜啊。一阵狂暴的疯狂过后,他疲倦了,他无力软弱地躺在小径旁的草地上,透过小径林上枝梢看着那月光从他的脸上从左颊到右颊慢慢地走过,他才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的冷静,渐渐地在他的脑海里悄悄地滋长,最后让他难以相信,他竟然在倏然间清醒过来了。
山林是寂寞的,小径是寂寞的,他们曾经喧闹过,他们曾经辉煌过,尽管世事沧桑夺取了他们的自豪和荣耀,但是他们却能够在失落和寂寞中默默地承受风雨雷电寒霜冷雪,承受由繁华到冷清的痛苦,而且毫无怨言、毫无抱恨地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沉默,依然在空旷的山谷固守着那份自我,依然用自己的执著在荒落的山野展示着自己的尊严,那是一种何等的伟大和静穆啊。
岁月在不停地走着从容的脚步,小径也在四季的轮回中依然走着自己的风景。春天来了,小径便幽静美丽地躺在那山花烂漫之中,静静地享受着春风的抚慰;夏天来了,小径被葱葱郁郁的林木紧紧地包裹着,沉醉在林涛美妙的乐曲中;秋天来了,小径在满山飘香的红叶中沉醉了;冬天来了,小径开始从激情中冷静下来,在沉默中等待那晶莹的雪花为自己披上一袭羽衣。
在繁盛与衰败面前,小径没有荣辱得失的喜怒,没有宁静与繁华的快痛。无论任何时候,他都保持着自己的超然,都执著着自己的沉默,那是一种境界,那是一种风流。
而他,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沧海一粟,却不能承受生活的挫折和打击,却不能保持自己人生的底线,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唉声叹气,委靡不振,自暴自弃,亵渎自己,那简直是在污辱自然的清净,玷污自然的纯洁!那是何等的卑微与怯弱!
人往往是在一个怦然心动的时候突发灵性而悟透人生的道理的。一阵宣泄过后的冷静,使他清醒多了,他无法容忍自己心灵的狭隘,在茫茫沉静的夜色里,他感觉自己应该和小径一样,做一个孤独的舞者。在这个舞蹈中,他变成了一只蛹,在长长厚厚的丝茧的包裹中,艰难地蠕动着躯体,最后把那银色网织的恐怖一点点地捅破,于是梦在苦疼中挣扎成美丽的蝶儿,穿过卑俗的空谷,舞动着一个孤寂而圣洁的灵魂,飞向了黎明。
篇二:民歌情结
喜爱民歌,每当听起,感觉一如初恋,纯美且遐想烂漫。
记得第一次听《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那美妙的韵律带着思绪飞翔,仿佛看到了满坡满野的茉莉花,夜空也变得诗意而且宁静,自己感到笑声也纯如山野泉水了。为了感受那种美的浸润,买了笛子,每晚练得入迷,虽然笛声粗劣,但沉浸其中的感觉一如和月亮对话。后来又买了音响每天一早一晚的放,茉莉花的香气似乎飘到了梦乡,永远印证着少女时代的浪漫,印证着那如茉莉花一样美的青春岁月。
对音乐的欣赏没有年龄界限,我的痴迷和爱好竟然节外生枝,陶冶出一位小音乐迷,那是邻家的一个小男孩,是我离开了乡村以后才知道的,他妈妈说,每当我放音乐的时候,小男孩就站在墙边痴痴的听,任怎么喊也不动。后来,我走了,不再有音乐声了,小孩情绪很低落,问谁欺负了他,才痴痴的说,我想听姑姑放音乐。
《月光下的凤尾竹》,让我对山寨竹楼痴迷,想着这月亮下的静谧和美妙,芭蕉叶下一定会有梅花鹿也沉醉在美妙的葫芦笙里,那如雾的凤尾竹是怎样的一种风情。和这种境界相比,华灯不再梦幻,柏油马路不再浪漫,于是云南的大理的山寨成了我青春梦想的伊甸园,心灵的栖息地。后来有机会到了大理,真的有到了家的感觉。凤尾竹依然青青,竹楼的姑娘依然美如珍珠。
每次参加联欢会,我最爱的选择就是民歌,唱过《天涯歌女》,《采红菱》,《在《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又会让我心灵澄澈,身边只剩月光流水。
那遥远的地方》,《敖包相会》等等,常唱常新,流行歌曲也很美,我也喜欢,像《荷塘月色》,《套马杆》,《我要去西藏》,《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等等,唱过就放一边了,没有民歌那样持久的魅力,永远占据心灵。
今夜一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又会让我心灵澄澈,身旁只剩月光流水。
篇三:酸菜情结
有朋久居他乡,近日归里省亲,几经寻觅,在我不经意之间,突然闯入了我的陋室。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君幼时与我相交甚厚,感情颇深。自从他考上大学之后至今二十余载,相互间只是略传书信,未曾谋面。今日久别重逢,其惊喜之度难以名状。二人交臂呃叹,打诺寒喧之后,我便草草收拾了几道家常小菜,拿出了至今仍生活在乡下的老同学送来的一坛子“老玉米”烧酒,二人便推杯举盏,相视对饮起来。
“啊哈,老兄,这是你自己腌制的吗?”这位仁兄诧异地用筷子指着一盘子酸菜问道。
“是啊,打小练就的手艺,几十年来未敢忘掉啊,”我回答说。
“地道,太地道啦!”他大口嚼着酸菜,筷子不停地往嘴里送,那样子好象要将那盘酸菜连盘子一同吞下去似的。
“慢点吃,老弟。我这里别的好东西没有,酸菜嘛,保你吃个够,只是别把牙酸倒了”。我端起被他几口吃光了的空盘子,到厨房的酸菜缸里又为他满满地捞了一盘子。
“老弟呀,出门几十年,看来还是忘不了咱这陕北的酸菜啊?”
“岂止是难忘啊,简直就是魂牵梦绕、刻骨铭心哪!”他端起酒杯,与我面前的酒杯碰了碰,脖子一扬,一饮而尽。之后又重重的咂巴了几下嘴巴,低着头深情地说道:
“几十年来走南闯北,跨海留洋,天下的山珍海味、奇特大餐我什麽没吃过?可就是咋也忘不了咱家乡的这口酸菜啊!有的时侯生了病,口淡无味,躺在病床上心里就想着:操他妈!如果这时候能来一碗酸菜,也许老子的病立马就会好啦!嘿嘿嘿嘿……”
他夹了一筷子酸菜塞到自己嘴里边嚼边说:“可惜,小时候我没有腌过酸菜,自己腌不了。有一年秋天,我实在是太想吃陕北酸菜了,突然就心血来潮,想自己腌点儿酸菜解解馋,于是就按照小时候看妈妈腌菜的程序,与老婆一起整整折腾了一整天,如法炮制地腌了一缸。接下来和老婆苦苦地期盼了一个多星期,他妈的!谁知道哪儿出了差错,我腌的菜吃起来又苦又咸,很是难吃,到最后还菜烂汤臭,只好全部到掉啦!为这事,老婆不知嘲笑了我多长时间呢!”说到这里,他自嘲地哈哈一笑。
听着他的絮叨,看着他对酸菜的那种痴恋乃至贪婪的样子,我的内心竟突然涌出一种温馨、亲切的感慨:
是啊!对于我们这些从小靠酸菜充饥、靠瓜菜维系生命的一代人来说,细细品来,的的确确会对这普普通通的“酸菜”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
我没有考证过,不知从何朝何代、何年何月开始,居住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人们,每逢深秋季节,家家户户便将整筐、整担、甚至是整车的大白菜、红黄萝卜等蔬菜往家拉。然后,全家尽其人力洗菜涮缸,切菜拌菜,完后将其装入足足有半人高的大瓷缸中,填满压实,经过数天的发酵后置于阴凉之处,于是,这便成了全家人整个冬季的主要副食品了。人口多的人家甚至要腌上几大缸才能保证全家人整个冬天的饮食所需。
在整个陕北地区,也会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地区方言、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不同的民风民俗。但就冬季储菜而言,整个陕北几乎均是采取这同一种方法,不同的只是酸菜的种类而已。
据我考证,陕北酸菜应分为两大类:即囫囵菜和碎菜两种:
所谓囫囵菜,顾名思义,就是把各种蔬菜洗净之后,不经过任何刀工切,将菜完整地装入缸内压实腌制。这种方法在整个陕北比较普遍,榆林和延安各地都有;
所谓碎菜,便是将各种蔬菜均切成段和丝,然后再装缸腌制。就蔬菜的种类而言,陕北酸菜几乎包容了全部的内容:大白菜、红、黄、白萝卜、芡莲、莲花白、豆角、黄瓜、芹菜、洋姜、地蝼等等。佐料配以葱、姜、蒜、辣椒、花椒、大料等。上好的酸菜腌制出来后,五颜六色、十分鲜艳,各种蔬菜尽展风采,吃到嘴里咸中带酸、酸中带甜、甜中有辣,嚼起来清脆爽口,具有一种特殊的清香,令人赞不绝口、不忍停箸。这种腌制方法主要分布在延安东南几个县才有。
陕北酸菜在吃法上也是花样繁多、特点各异,囫囵菜与碎菜的分类也就是为了在吃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同的烹饪方法,与其他食品搭配着食用才创制的。碎菜吃起来方便,无需任何加工,随时捞出一碗来就可以吃。有讲究者,浇以葱油、拌以辣面,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特别下饭。囫囵菜的用法相对就比较多,酸白菜可与冬贮的萝卜、土豆等烩菜、炖汤,也可与粉条、猪肉一起,烩成一道招待佳宾的上等佳肴。“酸菜熬洋芋”,“酸菜和面”,便是陕北每一个人乐于咀嚼的陕北名小吃;酸萝卜可以切片与大肉一同炒着吃,也可以切成细丝,置入辣椒面、味精、葱花,用热油炝之即可下饭,此亦是一道上好的下酒菜。
我从小就好吃酸菜,无论是吃馒头、吃窝头、吃面条,还是吃小米饭、喝小米粥,我都喜欢就着酸菜,而且每顿必是一大碗。那时候,每当妈妈烙烙饼的时候那便是我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刻。妈妈烙饼时,总是给饼里加上一种叫作“茨茉”的野草花,烙出的饼既酥又筋道。我吃饼的时候,喜欢把土豆丝和酸菜丝拌在一起,将其卷入大饼中,一咬一大口,吃起来十分地惬意,(当然这种惬意并非是常常有的)。在吃汤面或者喝稀饭时,总是和上半碗酸菜当饭吃。在那个“瓜代菜”的年月里,每当我放学回家晚了,母亲上工时留在锅里的红薯、土豆、南瓜等被弟妹们吃光了,我便捞上一大碗酸菜,冲上白开水——酸菜就白开水便可聊以充饥。为此,奶奶常常叫我是“菜虫”。
记得在县城读高中时,由于离家远而住校。学校的伙食极差,每顿饭就是一个名曰“半斤”的玉米面窝头,菜乃是五分钱一碗的白水煮萝卜汤。然而,每月三元钱的菜金消费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亦属一项高额的开支。因此,为了节省开支,我便常常不买菜吃,将窝头放在开水碗里用筷子戳碎,搁点食盐,就这样似饭非饭、似粥非粥,的确是难以下咽,然而,每天两顿饭仅此而已,不吃也得吃啊!
那年清明节那天,我们同宿舍的人正在吃中午开饭的时候,妈妈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当她看到十几个半大孩子围坐在铺着一张破席的大土炕上,每人端着一个大碗,吃着干涩的“窝头粥”时,妈妈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她慢慢地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拿出了两个老碗大的老馍馍(那是陕北人过清明节时特制的大花馍),将它一块一块地掰开,然后逐个送到每个同学的手里。大家捧着老馍馍,谁也说不出话来,但谁也没有将手中的馍送到嘴里。
我看到每位同学都是泪眼盈盈,泪水盈盈——
那个周末的晚上,我回到家以后,母亲却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次日,当我返校的时候,妈妈捞了一大盆囫囵酸菜切碎,破天荒地用油在锅里炝炒过之后,装入一个小瓷罐里,然后叮嘱我:“给每个同学分点儿,剩下的自己慢慢吃。”
到学校以后,恰巧宿舍里没人,于是,我就把菜罐藏在自己放书籍和衣物的箱子里。开饭的时候,看着十几个半大小子那种狼吞虎咽的劲头,我终于没有勇气将菜罐子拿出来。此后,每当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背着人悄悄地打开箱子,夹一筷子炒酸菜压在碗底,独自一人躲到一边去吃饭。
回到家里,我告诉母亲我是和学们共同分享了那坛子炒酸菜。看着母亲脸上溢出的笑容,我的内心感到十分惶愧。这件事儿,至今我都未敢在老母亲面前道破真相。
从那以后,每个周日下午,当我返校的时候,手里都提着那只瓷罐子,里面装满母亲认认真真炒好的酸菜。那瓷罐子,我提了读高中的两年时间。也就是这只酸菜罐子,后来伴随着我回乡劳动,伴随着我参加工作,伴随着我结婚成家,伴随着我生儿育女……十多年后,妻子不慎将那只罐子打碎了,为此,我与妻大吵一场,至今耿耿于怀!
成家以后,吃不到母亲腌的酸菜了。渐渐地,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每当秋季到来的时候,我便自己动手腌制起了酸菜。
从那以后,每年我都和母亲一样,腌上两缸:一缸囫囵菜,一缸碎菜。因我从小就经常帮助母亲腌菜,所以颇得母亲的真传,对腌菜的每一道程序均掌握得精熟,因此,我腌制的酸菜也颇受邻里们的青睐。每到吃饭的时候,经常有邻居拿着大碗上我们家索取酸菜,对此,我来者不拒,十分乐意地为他们捞上满满一大碗,并一再叮嘱他们吃完了再来捞。也许,隐约中有一种偿还高中时独自偷食酸菜的忏悔和歉疚的味道吧!
久而久之,我的酸菜和我腌制酸菜的手艺在单位便有了名气,每当有邻居或同事请我帮他们家腌酸菜时,我都乐此不疲,有时干脆亲手为他们腌制好,并亲传经验。仅此一事,我便在单位落了个极好的人缘。
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从小养就的饮食习惯,不管你的生活、地位发生什麽样的变化,他的饮食习惯终生都将难以改变。就因为我是吃着酸菜长大的,所以,养就了一种独特的饮食口味,没有酸菜就感到食而无味。因此,时至今日,我年年都会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地腌制酸菜。无论走到那里,无论我的生活发生什麽样的变化,总也改变不了我对酸菜的那种特殊的情结和独有的那份感受。每当吃饭的时候,即便是再好的宴席,假如没有了酸菜,我总是觉得提不起强烈的食欲来。我常常突发奇想:假如在大宴上,烹调生猛海蟹、龙虾鲍翅时,或配以上好的陕北酸菜,那味道一定别有洞天,另是一番滋味吧!
无论如何,我对酸菜情有独钟!因为有了酸菜,我便可以吃得下世界上任何难以下咽的饭食!
我的一生,注定要与酸菜结下不解之缘,注定是要与酸菜终生为伍了,乃至于也许在我弥留之际也一定会口衔着酸菜方能冥目九泉……
篇四:豆角情结
纤细的竹竿搭起了锥体型的架,豆角秧翘展着触须,一路欢歌的爬到了架顶,乳白的小花送来了细长的豆角,豆角像个调皮的娃娃,悠闲地在晨风里荡着秋千。满架的豆角细细长长,俊秀飘逸,远远望去,恰似一架风铃在晨光里演奏着美妙的乐曲。
豆角成熟了,扎成一捆捆,摆在了菜架上。这时候,妈妈总爱说:“有新鲜的豆角了,又能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豆角猪肉包子了。”这时候,妈妈也总会买上新鲜的豆角和猪肉,用酵母发好面,白白的面皮,翠绿的豆角馅,在妈妈的手里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个八面玲珑的可爱的包子。包子蒸熟了,芳香四溢。每次我都会迫不及待的拿一个深情的咬一口,妈妈每次也总会问:“怎么样,香不香?”“香,可好吃了。”妈妈便会看着我,把一个包子一口一口的吃完。也许,在妈妈的眼里,这时候的我,就是一个贪吃的孩子,正贪婪的享受着美味;可是在我的心里,这时候的我,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正贪婪的享受着母爱情深。妈妈是幸福的,她做出了世界上女儿最喜欢吃的美味。其实妈妈也知道,每年的豆角包子,女儿捧在手里的是一种情结,吃下去的是一种回忆。
每次捧着豆角包子,我总会想起高三那年吃包子的情景。中午下课了,我正要穿过偌大的操场去学校的食堂拿我的馒头,这时候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我,她告诉我,学校食堂中午做的豆角猪肉包子真诱人,可惜她只有菜票,没有馒头票,她肯定知道我有馒头票,因此提议中午的饭合伙吃了,我爽快的答应了。忘记了以前吃没吃过豆角猪肉包子,但那天的包子我肯定很想吃的。上高三的时候,家境不富裕,每个中午的饭大多数馒头加咸菜对付着解决,内心里是很渴望吃包子的。记得我俩高高兴兴的从食堂买了包子,回到她的寝室,爬到上铺她的床上,俩人对坐着,守着包子,你一个我一个的贪婪的吃了起了,一边吃一边啧啧赞叹:“好吃”“嗯,好吃”。那么好吃的包子,最后一个,俩人掰开,一人一半,和着满足吃下了肚。青葱的学生时代早已结束,那远去的豆角猪肉包子的清香似乎还在嘴边荡漾;扎着羊角辫的少女时代渐渐走远,那份纯洁的情意似乎永远围绕身边。
那顿包子至今难忘,不知为什么,以后的包子,只能吃出深深的情意,却再也无法吃出香甜。忽的想起一代明君朱元璋,落难时,乞讨吃过一顿香甜的珍珠白玉汤,称帝后,无法忘怀,但是再吃,已无当年的滋味。我自然无法与一代明君相提并论,但我私下想,吃前后的心情可能是一样的。
如今的生活,好吃的有营养的东西自然多过豆角包子,但豆角成熟的季节,依然年年都吃豆角猪肉包子。妈妈做的豆角包子依然伴着浓浓的情意,送我香甜的回忆!
篇五:草根情结
大地给予了人们众多的馈赠,生命和养活生命的物质财富。蔬菜便是其中最为绝妙的物品。家乡人把蔬菜称为“小菜”。小菜,自然是相对于鱼肉荤腥而言的。有客人来了,新鲜的小菜摆满了待客的饭桌。父亲总是再三对客人说:“都是小菜,真不好意思。”说的是客套话,事实上,农家待客的那份心意却实在而纯朴。
在我现居住地方,从窗口经常能看到一些人在垦荒种菜。住房的南边是一片泥地,建楼的备用地基,平时杂草丛生龌龊不堪,经过人们的整葺,种植了各种蔬菜,最里边的一簇是郁郁葱葱的花菜,如一条墨绿的毯子围着它的是长长的红薯的藤蔓;有风拂过时,水珠便从木瓜树的叶子上滴下,在山芋宽大的绿叶间摇晃成晶莹剔透的玛瑙。俨然一派生机盎然,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这情景常常会勾起我对家的怀念。只是这里的菜地没有小鸟,没有四处游荡的鸡群,没有我熟悉的稻草人,特别是菜地的四周没有篱笆,这常常让我有些怅然若失。在我家的老宅后面,有一块菜地。从我懂事起就是母亲在劳作。现在荒废已久,杂草丛生,早没有当年那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别老家近二十年来,它始终像一幅精美的工笔画,深深地嵌在我记忆的画框里。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在离家十多里一个村小任教,生活的重担落到了母亲的肩上。记忆中母亲总是早出晚归,里里外外一把手。白天在生产队里“抢工分,获取一家人的口粮。清早或傍晚,利用生产的间隙,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忙着在菜地里伺弄那些瓜果蔬菜。我们一家的零用开销,几姊妹的书学费,全靠这块菜地。母亲是个很会计划的人。一年四季不让它空闲,而且高矮作物套作,让它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比如,种下了旱菜的地中,她按行栽了几十棵辣椒,等到旱菜吃得差不多时,辣椒也长到尺来高,不久便可以收获了。这“间种”“套种”的方法她是早就掌握并使用了的。诸如她会把地边巧加利用,栽上高粱、菜豌豆、玉米之类。到夏日旺季时,菜地里满是花样繁多的菜式:葱、韭菜、竹叶菜、旱菜、黄瓜、辣椒、茄子、番茄、扁豆、豇豆、苞菜……满眼琳琅,赏心悦目!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时节是种瓜菜的最佳时令,早在乍暖还寒的二月,母亲开始下种了,尽管隔冬的白菜青菜萝卜蒜苗依然翠绿发亮,葱葱茏茏铺满整个菜地。母亲却张罗着,把去年收藏好的黄瓜,葫芦,豇豆,耳子菜,鹅米豆的种子,小心翼翼的取出来,打开一层一层棕布,看着这些种子,一粒粒亮晶晶黄灿灿饱满鼓胀。母亲的眼睛立刻光亮了许多,仿佛看到了一年的希望,我总是不解的问:地里还有那么多菜,又要下种?母亲摸着我的头意味深长的说:瓜菜赶早,才有好价钱啊。
鸡鸣头茬,娥眉月还斜挂在树梢。村子还在酣睡,母亲已悄悄地起床,借着月光,在菜地里忙开了,这些瓜苗豆秧,得赶农时,耽误不得,耽一时,误一季啊。母亲拔去那些依旧茂盛的冬菜,用锄头翻开泥土,躬身捡出草根石子,平整出一垄垄整齐的菜畦,极小心的把瓜苗豆秧捧在手心,轻轻地,柔柔的一棵一棵放进“窝”去,生怕它们受一点伤害,在周围洒些肥沃的细土,浇少许淡淡的粪水。外面用竹条编成笼子罩住,最后盖上稻草。把菜地拾掇好了,天才蒙蒙亮,这时我们还在甜蜜的梦乡里。
此后,母亲每天从生产队里收工回来,拖着疲惫的身子,有时连饭都顾不得吃,也总要去菜地里转转,拔草,施肥,捉虫。人勤地不懒,由于下种时间早,加之母亲的精心管理,往往是端午节前后,瓜果豆荚,已经热热闹闹挂满了整个园子:憨憨呆呆的南瓜,青嫩顶刺的黄瓜,紫里透青的鹅米豆,在葱郁的叶蔓间,时隐时现,尺把长的豇豆,密密匝匝的吊弯了豆架,肥嫩的四季豆,汁液饱胀翠色欲流……就连菜地边的竹篱笆上,高高低低的吊着苦瓜,而别人家地里的瓜菜才开花呢!母亲将这些瓜果豆荚采摘下来,背到乡场上,总是被抢购一空。蔬菜赶早,谁不想尝个鲜?母亲回家时的背篓里,放着肥皂火柴食盐和绿绿的新衣服。母亲微笑着说这是南瓜钱买的衣服,那是豇豆钱买书包,那是鹅米豆钱买的裙子……
那时候,我很喜欢和母亲去菜地,一般都是傍晚时分,夕阳暖暖地照着,空旷的田野已弥散着淡淡的烟火味。母亲一边摘菜或浇菜,一边和另一菜地里的三婶六婆说着各自的菜生长情况或者预计下一步种点什么。而我最喜欢钻进两排瓜豆间的过道。茂盛的叶子已把这围城了一个绿色的狭长的帐篷,即使是夏日的中午里面也很阴凉,但并不寂静。一条条修长的豆角悠然地伸展着,一个个憨厚的冬瓜腆着肚子,四处觅食的蜂蝶、虫子、小青蛙在花叶间在地里流连,黄色的冬瓜、丝瓜花,粉紫色的豆角花都成了它们探寻的对象。我坐在绿色的“帐篷”里,一边玩着泥土,一边看着它们,有时也会恶作剧地把一只七星虫从一张叶子抓到另一张叶子,让它深受一番困苦。那时我还不懂什么痛苦快乐,世界对我来说那样新鲜,一个菜地是取之不绝的乐园。
在那个物质相对比较匮乏的年代,生产队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菜地就成了聚宝盆。不仅保证一家人吃的蔬菜,还要种一些红薯、玉米、大豆等经济作物,以弥补粮食的不足。一日三餐,没有一顿全是白米饭。早上要掺着红薯或萝卜煮粥,中午是红薯丝或萝卜丝和着米饭一起蒸。晚上每人只有小半碗饭,其余是吃杂粮。母亲劳作的菜地,以翠绿连着四季,将一家人艰难的日子,连缀成一条曲折而又艰难的生命线。母亲,曾用她那不懈的劳作度过艰难的岁月,最难熬的就是每年青黄不接的“三荒四月”。在揭不开锅的时候,父亲把床底下落满尘埃的南瓜搬出来,小心翼翼地切开,在我们的眼里,那简直就是杀了一头猪,可以足足地让我们体会兴奋和急切,兄妹几人因为可以饱餐一顿而高兴得手舞足蹈。记得最清晰的一次是半夜里被饿醒,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问母亲要吃的,家里实在没有过夜粮,母亲就摸黑到菜地里,摘了两条还没有掉花蒂的黄瓜给我,度过难熬的夜晚。那些年月,青菜、红薯、南瓜、豆角都曾经用来填饱我们成长岁月里的辘辘饥肠。看着我们吃饱之后满足的样子,母亲脸上却没有笑容,只有泪水。
上中学时我在校寄宿,假期里回到家,必要去菜地去看看。有时进不了门,便想着母亲必在菜地无疑。看到她在地里忙碌,已能体谅母亲的辛劳,尽可能帮助母亲分担生活的重担,拔草、松土、间苗、浇水、施肥、收割,样样都做。往往在这时,母亲摘下翠生生的,有着尖尖嫩剌芽儿的黄瓜,或红透了的西红柿让我吃,那味道极鲜美着呢,比起现今在市场上买来的不知要香甜多少倍。碰上农忙的时候,我干不了重活,母亲就让我在家做饭、养猪。每天到菜地采摘蔬菜瓜果,或者摘黄菜叶、割红薯藤养猪。吃不完的瓜菜,母亲做成咸菜,撒上红辣椒,五香粉,风味独特。每次上学,母亲用瓶罐装上自制的咸菜,陪伴着我的读书时光。到现在还十分怀念母亲自做的坛子菜。菜地既是我童年的乐园,也让我很早就品尝到生活的艰难。现在对比体味,在母亲的菜园里翻阅要比流连在人们用文字构成的花园更让我舒心快慰!
从我在床上听着母亲挖地的声音,到现在,再看着母亲佝偻着背的身影,这中间一晃就是几十年的时光。或许,光阴的脚步,就是从这一片又一片的菜地,菜地里一茬又一茬青了又黄,黄了又青的蔬菜里飞逝的吧。而母亲的头发,也在这流转的光阴中日渐地花白稀疏了,在秋阳下泛着一层微微黄色的光晕。
现代人很多远离了土地,我总觉得是有所欠缺的。我的双手不沾泥土很久了,有时无意沾上了,也视之为脏物,快速的将其洗去。一颗视泥土为脏物的心灵是不懂母亲的意义的,因为大地就是母亲!
如今又是一年的秋天,住房前地里的菜快收完了,人们就把那些藤藤蔓蔓收拢来烧作肥料,傍晚的时候,一股青烟在地里升腾,菜叶、菜枝、菜藤的香味混合着,慢慢地在天空飘散,一直弥漫到我的心底,在每一个秋天来临时,都从我的记忆里飘荡出来。
本文由散文网用户整理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