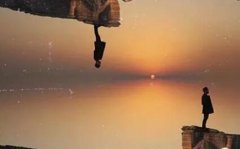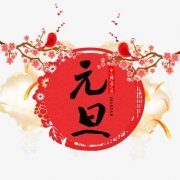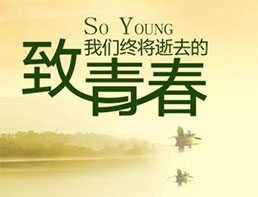关于情节的文章
2019-04-09 22:05 来源:散文网
篇一:紫菊情节
我喜欢菊花,更喜欢紫色。尤其是那种淡淡的梦幻般的紫色,更能驰骋自己的想象,但紫色并不十分与我协调,因为她太现代,而我却如同属于过去的时代。
想起小时侯,在我家乡附近有个小花园,到处盛开着淡淡的似云如雾的紫菊,一串串玲珑斜逸而出的花儿,使她更显生动。美丽。幼时我常在这花园玩耍,常常会去采摘花朵,用针线小心地串起,当作项链,头饰。为此,常给小伙伴们取笑,好漂亮的新娘。
在紫菊的氛围中,我度过了童年。回到了上海,离开了我那梦幻般紫色的花园,从此紫菊的氛围就只有留在我的心中……
于是,我试图从服饰上弥补,但由于我气质与紫色的格格不入,这种企图也如肥皂泡般破裂。我开始怀疑我是否不配喜爱,不配拥有紫色。这种典雅。高贵,浪漫,神秘的色彩,一下令我感到羞愧,似乎不敢再去追求,但心底的深爱却又那样执著,便又怕亵渎了紫色。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更偏爱紫色,通灵的紫色,仿佛时时会随我的心情而变。沉郁。清朗。热烈。
记得05年我回到了家乡——-江西沙汾,儿时的伙伴,聚际一堂。只见花园依在,紫色满圆,心中的紫色和满目的紫菊立刻交融在一起。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我绽放的徽笑和紫菊花一起盛开。
紫菊是我的最爱,当我有了号时,我用紫菊作为我的昵称,为的是激励自己不在消沉,当我开通了空间时,我用紫菊来映衬我的家园…。
紫菊依然是我心中的情。最近我又开通了博客,用紫菊开启我的一扇心门,迎接飘逸恬雅的字香。眷念,那如花如开的情系和永不褪色的情怀。那一缕淡淡的菊香,在飘移的岁月让往事轻轻叩响,菊香里任由记忆缓步走来,留下一路芬芳。守望繁星点缀的夜空,心绪飞扬。心灵的帷幕几分欢悦几多忧愁,却是在寂寞的时刻拉开悠长的记忆……
感恩记忆里盈香的紫菊,轻轻呼唤着岁月馈赠的深情。感恩记忆里怡然的紫菊,细细咀嚼着生命赐予的感动。在那紫菊的幽香中,遨游畅想着梦幻般的紫色。。。。
我爱紫菊,爱她给我的回忆,爱她能给我心灵的解脱和活力,对紫菊的回忆,永远是我心中的情结。
篇二:我的安妮情节
安妮的小说里总是有一个男人,叫他林。他是一个在写字楼里随处可见而又无法捕捉的小小白领。林,一个人住,寂寞,空虚,喜欢黑暗。这样的人不能遭遇爱情,因为那就是一场劫难。总有一个女人,叫她乔。为什么安妮每次都让她疼痛地去爱过之后。又静悄悄地死去。我每次都不想读故事的结局。我真的不想让她死。
乔,总让我感到窒息。
其实,安妮的许多故事都有一样的天气,一样的情节,一样的咖啡,一样的冷漠的相处之后,又是一样的结局。但我总是不可遏制的翻开下一页。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丢掉了所有她的文字,我一定是老去了。
我常常想,人应该如何决绝地处理自己。可是,生活已经把我们折磨地半死不活了。在这些潮湿的文字里,会有一个女孩,她的邪气慧黠的腔调,那些晦涩简单的语句。未曾见过这样冰雪般凛冽的女孩。她说,大海是地球最清澈温暖的一颗眼泪。就是这样热爱着蓝色的人,却不断地沉溺,再沉溺。
那是一些阴郁而美丽的文字,一些酷烈而凄艳的言情故事。关于一个着白棉布裙,光脚穿球鞋的年轻女人。一个没有承担的男人。关于一个并不被死亡所终结的心碎。关于麻木中绽裂的伤口,在沉溺与自弃中的清醒与冷眼。
都市——这个不断被虚构的空间。那是永远的漂泊流浪的现代森林,也是无家可归者的唯一归属。在那里,生命如同脆弱的琴弦。个人如同漂泊中的落叶,期间闪烁着一份将熄的灰烬里艳丽的血色。如同在一幅极端幽暗,而蕴藏威胁的背景上显露出的色彩斑斓而饱满的憧憬幻影。迷人,伤痕和狰狞。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祝福的声音,只有苦苦的坚守。希望能够用乐观而坚强的外表把自己包裹,听见你一次次地告诉我,你不会爱上我。我总是陷入别人的生活中,活在别人的文字里,死在不知所终的岔路口。有一天,当我发现有人用笔画出我的心的轮廓的时候,我不自觉的爱了,好像故事中是我在活生生地演绎,也许结局让我心有不甘,但我却既不抱怨也不想改变。
原来,宿命是本质的东西。不管我喜不喜欢,是我的,就永远都丢不掉。
那么,与其徒劳无果,不如让过程更灿烂一点吧!
篇三:情节,一曲离歌
又到情人节了。这样的节日于我而言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就算是庆祝我也不懂得该如何施舍这令人无奈的时间。曾揣摩过一些字句,其中很多包括美好的回忆、情感以及温暖的往事,总是将自己放置其中,幻想那些遥远的幸福,虽然只是浅薄的理会。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贫乏的精神所在才让我一度的自卑无力。于是,我将所有的话语都划上了悲情的句号。
静静的阳光下,又泛起了童话般的想象,着属于明媚的忧伤,淡淡的愁苦,想着自己怎样让一切破碎,怎样象飞娥扑火,捕捉着心底凄楚的欣慰。我知道,自己永远在时角的最深处,鳞体上始终保留着那一处殇的疤痕,没有人能触及到它,更无法治愈。
回首看那每一次令我伤感的痕迹,一次次又将痛楚,流离在依然散发孤单味道的冬季里。又一次飘雪的日子,慢慢随时间远去,而我只能让以后的记忆空着,让童话的木屋空着;我不关心缺憾是否属于悲剧怎样延伸的美,我不关心自己怎样背负着憧憬失落后的沉重,在流落中步履维艰;我只关心,我能否拥有最终释怀的酸楚,孤独的欣慰……(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悲剧或者一些生命的缺憾总会成为久久不能散去时间的背景,也许正因为这些残缺或者无法拥有,自己知道在存在的过程中,也总会刻下那些深深浅浅,或伤或痛的辗转的轨迹,或许一生我们都在沿着这条永远无法完满的曲线,一路停停走走。
在路之初始,在有路或者无路时候,隔着人的此岸,彼岸,不必向往,那只是一段生生相错的悲情,有足够的凄美,带给你的是无限的感伤。但我不知道,这究竟属于一段过错,还是一段甘愿的承受,我只能再次在风中,携起时间之手……
过往种种,再多的不舍,再多的凄美,也只能埋藏在心湖的最底部,当一切随烟消失的时候,惟有沉默着走下烽火的祭坛;泪染红尘,需要用清澈的痛,来放大那些不曾在意的细微,然后让对过往的感慨在路上低回。
情感的流离,不能以驿站的方式栖居,关于最后,关于期许,该在记忆里沉默,用遗憾锻造最真实的凝重。我想,这即是童话里最平凡的结局吧。
记忆燃烧,同枯萎无关。心,总还是要沉默着走下祭坛,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感叹在茫茫人海消失的身影……
篇四:飘落在他乡的异国情节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无论是黑夜或者是白天,只要一有闲暇,这个问题就会烟雾一样缓缓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然后丝丝缕缕地扩散。
相对于现在,过去总是年轻的。年轻而灿烂、激情四射,令人羡慕而怀念。回忆过去好像应该是一个老年人的事,所以我总是在想我是不是老了。或者,青春就像一张驴皮,在我的生命里已经只剩下了一个驴尾巴。
这是不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生命尚未终结,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每一天都像是一枚生活的碎片,无法预知它们最后会拼贴出一个怎么样的形态。谁也不能确定故事会在哪一个段落戛然而止,达到真正的终结。也许就在明天,也许是永远,也许根本就没有终结。
时间似乎悄悄地来到了2004年。2004年我离开越南时也是在这个季节。我把最后一次发表在深圳《大鹏湾》的一首诗送给了唯一去车站送我的水品。那一天是她的30岁生日。在开完她的生日Party,我说我要走了,我要回那个给予我生命的城市。水品跟着车跑了很远,我把那首诗扔给了她,那首诗题叫《无题》。我想我会把她忘了,虽然她为我付出了她的一切,但每当在这个秋风习习,红叶满地的时候,往事不由自主地在眼前纷至沓来,我却发现,原来我还是一直在深深地怀念着她。
我想,人与人的相识与分别原来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与水品的那段日子,说不出是不是缘。水品是胡志明市一家杂志社的编辑,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去过中国许多名山大川,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让我叹负不已。她在看了我写的那篇《失恋了真好》的作品后打电话约我去和她面谈。她说我的文学中悲观气息太浓了,那样不宜发表,她问我能否再改一改。见到她时,她惊讶地对我说,没想到你看起来还像个大孩子。这句话使我在内心深处把她看成了我的好姐姐。
水品是个温柔而多愁善感的女人,她给我审过多篇稿,与她交往的那段日子里,我总看到她一个人。后来我才知道曾经有一个中国男人深深地爱过她。那个男人在深圳,是一家杂志社的主编。当时那男人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他说他可以为她离婚。水品抱着他可爱的小女儿对他说不行。他说如果没有水品,他的生活就会失去色彩,他将会去死。水品说:“好吧,我答应你,但为了孩子你不能离婚。”
那是在8年前,水品还是个青春少女。那个男人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水品。水品是这么想的。他们苦恋了6年。有一天,水品突然发现其实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爱,又不知爱该用什么方式表达。她突然发现自己在犯了一个大错,于是她就走了,那个男人没有挽留她,也没有去送她,后来水品说,其实他们彼此都已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分手也许是最好的结局。我第一次称呼她为“水品姐”时,她感到很吃惊,她问我她是不是很老了,我说不是。她摇摇头说别骗我了。8年,我的青春不在了。
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过被爱棘伤的痛苦,那是在高中时与萍的一段爱情。我谒力相信自己,在这个匆忙的人群和浮华的尘世中,除了我脚下踩着的这方寸土地,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的心。我为了失去的那段恋情,离开了故乡,独自一人去了深圳,并且也不想再去触动那颗受伤过的心。后来因工作的需要,我被公司调到了越南。
认识水品是在顺化的一次展销会上。与水品的交往,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水品人还是长得挺美,在经过一段婚外恋情显得更成熟、丰满,该大的地方不小,该小的地方不大,常常披一头柔韧的秀发也吸引着许多异性们的眼光。而最让我对水品有好感的是在我那次重病。当时的我穷得连买日用品的钱都没有。我想我差不多要死了,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可怜,我死了,在这国外也许还会累了劳累一生的父母,但在这时我又很想见到他们,那怕是看一眼。伤心之中我想起了水品,我打了个电话给她,我说我要“走”了。聪明的水品在电话里就听出了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急忙找到我,把我送进医院。医生诊断我得胃溃疡,需要住院接受治疗。水品问我怎么会弄成这样,我告诉她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有胃病了,只因为家里要送我上学,就没钱再给我治病了。水品给我削了个苹果,她对我说只要有她在我身边我不会死的,肯定不会死的,并且要我安心养病。
茫茫人海,只因为流浪让我在异国他乡认识了水品,而水品每天总是一下了班就跑到医院来看我。每次她总会小心翼翼地削一个苹果给我。水品的热情让我感激涕零,我说我觉得自己还不如苹果里的一条虫子。水品问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为什么不把病养好。其实这些年我也说不清楚。由于自己的文化低,我在建筑工地做过小工,在菜场种过菜,在砖厂做过泥水工,甚至还捡过废品,后来在深圳这边进了现在的工厂,业余时间就趴在床上爬格子,写出来的文字能否成文成章,自己也没有真正想过,不过也能歉点稿费填填肚皮……在我的故事里,我看到水品眼中的泪水随时间悄然滑落。那一刻,我发现水品其实很年轻,目光清澈,嘴唇鲜嫩,长发如水,就像她的名字在我的心里一阵燥动。
至今我想,如果没有水品,我也许不会活到今天,也可能不是也许,而是肯定不会活到今天。在我走出医院时,我想我欠水品的也许在今生都还不清,但我决心一定要还给她。我要拼命歉钱,拼命写稿,甚至要水品介绍我去做兼职。我把生活费之外的钱全部给了水品,我常常对自己说,我要在最快的时间里把欠水品的钱全部还清。虽然我知道我欠水品的并非仅仅是钱。水品总是说够了,已经还清了。最后她说帮我把钱存起来。
直到有一天,她从银行取出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现款,她说要把这钱全部换成外币,她说她想离开周围熟悉的人群,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她说她有个舅舅在加拿大,将会帮她办移民去那边。她问我想不想去,我说我只是一个一名不文的寒士,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她犹豫了片刻,忽然对我说我们结婚吧。说完,她又哭了起来,边哭边说她知道要与我结婚是痴心妄想,她说她已配不上我,给别人做了6年的情妇,年龄又比我还大……我呆呆地望着她,最后我说让我想一想吧。
我想了很长时间。我发现有许多内心深处的情感,我们永远也理不清。我对水品说你自己去加拿大吧,我永远只会把你当做我的姐姐,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么我只会给你带来痛苦。我说我也要走了。
当这个夜晚即将离去之前我完成了这个故事。当我校完这千字小文,午夜的钟声早已响过。我推开阳台的门,已感觉不到秋季的清爽。不经意间,发现那参天的梧桐的叶子,默然的落到花架,又跌落到阳台,哒哒作响。静谧的天空,似乎也湛蓝了许多,天际的繁星,依旧的灿烂,好象无关于秋的离去。悬然于空中的残月,倒让我的心房稍稍震颤,虽已不在圆满,确是那样的明媚,明媚的让人心碎。忽然我发现每个人一生中的旅途都是双重的。我们将要走的和我们已经走过的路在回忆中又将寻着旧迹走回去。
最后我想起水品站在国际机场送我回国的那一刻,我深切的感受到她眼里分明闪动着爱情远去的泪水,可她努力着不让自己在这一刻流出来,直摇着手呼着我的名字,她的呼声在我耳边响着久久的回音。今夜,我想起她的影子在我眼前慢慢消失……
篇五:窝窝情节
每次我见到窝窝头,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好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亲切,又像朝夕相处的爱人那样温存。从三、四岁记事开始,一直到十八岁上大学,在我全部的记忆里,最深刻、最闪光、最持久的内容,就是窝窝。一年365天里就有364天,一天三顿饭就有四次进食窝窝,吃得很香很甜,简直就是狼吞虎咽。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在任何情景下,我只要看到窝窝头,不管是什么形状,不管是怎样大小,不管是用什么面粉做成的,都能瞬间把我带到属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
我出生在1959年9月的鲁西南大平原。那是一个贫穷得不能再贫穷的地方,是一个饥饿肆虏的年月。听老人说附近几个村庄里,孩子没有了上学玩耍的气力,大人没有了下地劳作的力气,坐在门槛上,蹲在墙根下,骨瘦如柴,全身软软得像棉花,眼睛垂垂得像铃铛,脸上又黄又黑,像等死的肝癌病人,慢慢地大半去了那个不用吃饭的世界里。
那年我们村里没有饿死人。母亲说是村支书明白,没有全听别人的话,领着全村老小把去年秋天的地瓜收了回来,晒成了瓜干,做成了窝窝,每人每天分给两个窝窝,才熬过了那个鬼门关;父亲说是村长有经验,在去年收了地瓜后种上了满坡的胡萝卜,储在地窖里,才度过了那个和死神打架的槛。不管咋着,二老说的是一个人,是一件事。
到我记事时,景况有了好转,村里人都能吃上了地瓜窝窝。刚记事的孩子就对两件事情感到幸福和甜蜜,一是吃饭,二是玩耍。那时不知道别的东西好吃,能吃饱地瓜面窝窝,有时还可以就着块咸萝卜,喝着地瓜面糊涂就非常满足了。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发现自己有了爱好,比任何玩耍项目都有兴趣,这就是看母亲做窝窝。
母亲是个做事很利落的人,蒸地瓜窝窝,馇地瓜糊涂是她的拿手活。地瓜面是灰白色的,母亲用面瓢把面挖在大瓷盆里,然后加入一定量的温水,拌匀后用手揣揉,里面还要放些火碱。母亲揣面很有力量,不一会就好了。然后就是做窝窝,揪一块面放在左手里,先用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在面团的中央摁出窝来,继续摁下去,窝越来越大,一眨眼工夫一个窝窝就做成了,象变魔术一样,不一会一大锅窝窝就做好了。小时候经常看母亲做窝窝,比在戏院子里看魔术师的精彩表演还开心。窝窝做好后,母亲用厚厚的木制锅盖盖上八窨大锅,然后就烧火,我为了取悦母亲,帮着抱柴火,由于年龄小,时常帮倒忙,惹得母亲不高兴。一刻功夫锅里边向外冒出很大的蒸汽,母亲说声好了,停下火就去忙别的家务,那时家中人多,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我,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母亲总有干不完的活。不一会,在我和弟弟妹妹的一再催促下,母亲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去厨房掀锅。
掀锅对我和弟弟妹妹来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大木锅盖掀开后,锅里的蒸气象天上浓浓的白云滚滚而上,蒸气散去后,窝窝清晰可见,又大又亮,整整齐齐,母亲把它拾到筐里,满满一大筐,象小山一样,我和弟、妹看着直流口水,母亲见孩子们饿了,赶忙每人分一个。我每次拿到窝窝,都要看一番再吃,也顾不上弟弟妹妹。窝窝拿在手里,象橡皮做的,稍一捏就扁,松开手马上就恢复原状,颜色灰里透些红,半透明状态,吃到嘴里要用力才行,很筋硬,嚼起来有苦苦的甜味,当时觉着真好吃。
感觉地瓜窝窝最好吃的时候还是高中阶段。记得是十六、七岁,是身体发育最快的年龄,饭量很大,一顿要吃十多个,一斤多干面的。那时住校,开学时把一个学期的地瓜干拉去,换成饭票。学校离家三里路,每周回家一次,每次回家主要任务是带地瓜窝窝,以备晚上自习后吃,所以每周给我做窝窝也就成了母亲的一项重活,每次一大布袋,需要两大锅。回到学校,把带来的窝窝分成小袋,挂在宿舍墙的钉子上。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学校里不抓学习,多数同学都不学,可我喜欢学习,每天晚上都学到很晚,寒冷的冬天也是如此,回到宿舍后肚子饿得咕咕叫,就从墙上摸着黑拿个窝窝吃。我怕影响同学睡觉,就到室外操场上吃,反正屋里屋外一个温度。我看看月亮冰冷冰冷的,听听周围死静死静的,只有肚子的叫声和我吃窝窝的声音,感觉很凄凉。咬一口窝窝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因为里边有很多冰冰碴,可是吃起来非常香甜,胜过现在的任何点心。窝窝拿在手里象个冰蛋子,冰得手又痛又麻,不断地这手倒那手。当时一想起家里父母和弟弟妹妹连这样的冰窝窝也吃不饱,心里就特别难受,眼泪从脸上滚落下来,象冰冰碴溶化的水,凉凉的流进了心里。
吃地瓜窝窝身体长得很快。可是只长个子和体重,就是不长力气,高中两年,长了二十公分高,增了三十多斤体重,俨然成了一个魁梧的成年男子,可力气不足,一有体育课就发愁,所以参加工作后就特别体谅中国足球队,吃地瓜喝糊涂长大的咋能和吃牛肉喝牛奶长大的一样拼呢?后来才知道地瓜的营养不全面,主要含淀粉,蛋白质含量很低。
其实,窝窝有很多种。那时地瓜面的占主,还有小米面的、玉米面的、掺了黄豆的杂面的;有掺野菜的、掺树叶的、掺鲜地瓜叶的,等等。我们家一直吃地瓜面的,是因为地瓜便宜,一斤玉米可换五斤地瓜干,一斤大豆可换十几斤,小麦换得更多。就这样每年还要缺几个月吃的。每到春荒时,父亲母亲到处找亲戚朋友借钱借粮,拿借来的钱再到几十里以外的另一个县去买地瓜干,那里的瓜干每斤便宜一分钱。拉着地排车,来回步行百里,我从十来岁就跟父亲拉地瓜干,一直到上大学,年年如此。由于家中缺吃的,父母常把仅有的窝窝省给我和弟弟妹妹吃,自己忍着,还要下地干重体力活,让人非常心疼。每每想起这些,心中就十分酸楚,泪珠子在眼眶里打转转。就是这么艰苦,二老从没间断过我们的学习。他们认准了一个理,吃不饱穿不暖,不怨天不怨地,就怨自己没文化,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
七七年恢复高考,二老的眼睛亮了起来。就象六月的连阴天突然出来了太阳。那年我已经高中毕业在家干了一年的农活,一年中父母操碎了心,想了很多办法,远近的亲戚邻居凡是在城里工作的,都找过了,求过了,甚至是哀求,其实就想当一名临时工,当时城里日子也不好过,就业很难,结果无济于事。到了下半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父亲异常的兴奋,把我送到县城里复习功课。邻居二叔在县城一家小学任校长,二叔的长子长我一岁,也在复习应考,于是我俩就白天一起学习,晚上一个被窝睡觉,复习了一个月,一起参加高考,可惜他落榜了,记得我很难过。当时吃饭成了问题,那时都不宽余,二叔每月二十几元的工资,要养一家老小。所以我只好从家带饭,放在老师锅里热热再吃。带的饭当然还是地瓜窝窝,有的老师给我开玩笑,说我的窝窝都把他的馒头串成地瓜味了。
父亲为了不耽误我学习,就把窝窝送到学校里。两、三天一趟,每次重重的一大袋。县城到我家十二华里,六十多岁的父亲步行要一个半小时,来回三个小时,正值三九严寒,非常辛苦。可父亲倒觉得很幸福,每次来了总是慈祥地看着我笑,搓一搓冻僵的手,擦一擦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然后把窝窝袋子亲手递到我手上。父亲知道我是个爱学的孩子,从不催我学习,倒是反复嘱咐不要学得太晚,要注意身体。我接过窝窝袋子,知道它的分量,也就不说什么。我仔细看看父亲,他很瘦很瘦,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个子接近一米八,体重不足一百斤,腰板挺的很直,象一个硬是挺着的麻杆,走起路来风一刮就有倒的危险,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让父亲承受起这么重的窝窝袋,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
父亲送来的窝窝,象一针针兴奋剂,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所以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第一想到的是父亲送来的窝窝和送窝窝的父亲,当然还有做窝窝的母亲。以后的多年里母亲做窝窝和父亲送窝窝的情景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每次梦醒时分心里总是酸酸的,总要静静地流一会眼泪才好受些。父亲去世时,我在外地出差,没能见上一面,所以一直感觉父亲还活着,十多年了经常梦到他老人家,梦里就好象回到了过去的平凡生活,一起干农活,一起吃地瓜窝窝,喝地瓜糊涂,后来才明白父亲一直活在我心里。
上大学以后,很少再吃到纯地瓜面的窝窝。回老家时有时让母亲做几个尝尝,但一直找不到过去的味道,要么怨地瓜施了化肥,变了品质,要么就认为母亲年事已高,做窝窝的技术水平下降了,反正吃不出原来的味道,又苦又涩,在嗓子眼里打转,就是咽不下去,好象成了天底下最难吃的食品。母亲看着我吃窝窝为难的样子,并没有生气,轻轻地说,地瓜窝窝本来就这样,不是窝窝的味道变了,而是现在好吃的东西多了,肚子不挨饿了。不管怎样,我对窝窝的感情丝毫没有改变,随着岁月的流失反而越来越深,越来越思念和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一起吃窝窝的日子。尽管它在当今食物中算不上上品,但是它毕竟养活了一代甚至几代对社会有用的人。
难怪清代翰林魏希徽晚年回家开窝窝店,并作赋赞颂窝窝呢!此翁是我老家郓城的一位历史名人,出身贫苦,幼年丧父,靠知书达理的母亲抚养成人。他勤奋好学,十多岁就能赋诗作文,二十岁乡试夺魁,三十岁金榜提名,康熙大帝亲点二甲第一,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成为皇室东宫日讲官,专门教授皇太子。他在朝三十年,六十岁告老还乡,在县城开了一家饭铺,专卖窝窝,价格很低,意在救济穷苦百姓。这个时期,写下了《窝窝赋》,感情丰富,脍炙人口。照此抄写下来,与读者朋友一起品味,去体会一下当初和现在的贫民生活。
“美哉窝窝兮,本天地之所产,由人力之所造,列五谷之班次,毓二气之精奥。田舍翁之常食,穷秀才之佳肴,与豆腐为同侣,共蒜酱而逍遥。米粥不如其实际,糊涂不如其坚牢,嗤包皮为假饰,与锅饼为同胞。类馍馍而无底,比烧饼而差高,相其形似将军之帽,观其色赛状元之袍。里二而外八兮,纤手成就,表实而中空兮,柔指均调。味当耐久,有终日之饱;每饭不离,无须臾之抛,富豪视尔为粗糟,吾辈看尔为旧交。孔子有之不必束水,颜回逢之何用箪瓢,於陵无尔三日不食,首阳无尔饿食菜苗。寒冬雪夜胜似羊羔美酒,价廉工省不用椒姜作料。但得与尔同味,愿与终身偕老”。
本文由散文网用户整理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