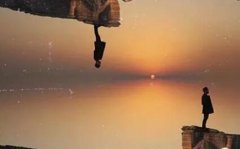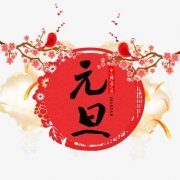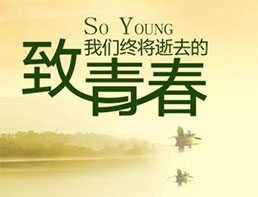关于困惑的文章
2019-04-09 22:04 来源:散文网
篇一:困惑
我好迷惑,哥不是传说,茫茫人海中到底谁是我的老婆?可怜如今我已是三十多,却依旧还是光棍一个。芸芸众生谁会成全我?陪我花前月下耳鬓厮磨,伴我小桥流水齐步快乐;共同搭建一个温暖的窝,一起无忧无虑幸福的生活!问风究竟是为什么,风不吱声一个劲儿的从我身边穿过;问雨到底是因何,雨不屑一顾继续瓢泼。
任凭岁月蹉跎,我流着汗水在太阳底下默默辛苦地工作;我不怕受微笑的冷落,但是不甘心爱情是一片沙漠。我不怕清凉如水宁静似夜般的寂寞,但是不情愿在人生中沉默。人家讲我是个不错的小伙,可为什么却没有人与我一起来掌舵?风雨黑暗中我一个人在摸索,虽然看不到伊甸园的轮廓,但是无论是激流是险阻我都选择了过河;面对千辛万苦我没有退缩,我一如既往的继续漂泊。为了幸福我一路奔波,总想抓住时代的脉搏;即使泪在心中凝结成一颗琥珀,也发誓决心要活也要活出个男子汉的气魄。
世上的玫瑰花那么多,为什么属于我的就没有一朵?滚滚红尘谁能看破?为爱有几个人不是失魂落魄?即使是征途坎坷,大雨滂沱,我也不肯闪躲;即使是暴风掀起旋涡,我也要驾着梦之舟在爱中沉没。
忧愁是一把无形的锁,让别有怀抱的人无力挣脱;希望却像一团燃烧得熊熊烈火,耀眼的光芒将黑夜编织的网狠狠地刺破。为了一个憧憬我在心中执着,只为在人群中等你回眸;虽然锦书难托,但是我相信这只是缘份的过错。把伤痛轻轻抚摸,谁又愿用心倾听我忧伤的欢乐?找不到患难之中一生不变的承诺,我有什么理由停止穿梭?哪怕是期待变成灰色泡沫,时间也会把伤口愈合;只要故事有一个美丽的结果,又何必在乎在情海中颠簸!午夜里的收音机深深传来一首歌,“……没有了爱情也要生活,抛开一切重新来过……”……
篇二:困惑
面对学生安吉的人生困惑而无解,我着实汗颜。
安吉是我最钟爱的学生。在体味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的两年北漂生活后,顾忌父母双亲的感受,他毅然回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我市某局公务员。超常的才华使他不到三年即从科员升至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他人长得又高又帅,虽不富,却是当时众多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就是这样一个令我自豪的学生,最近给我写了一封近乎遗书的长信,道出了人生的困惑。我阅后四顾茫然,现公开之,祈愿大智者帮我解之。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学生安吉顿首:俗话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学生以前自以为看透人生,目前却困惑得生不如死,不得已再烦老师指点迷津。
想我求学之时,在您的指导下,我博览经史子集,精研儒释道教,潜学内圣外王之道,立志修齐治平,只为将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时台湾作家柏杨著文喻社会为大染缸,我深不以为然。自觉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若荷花出污泥而不染者大有人在。故在我心灵深处早镌刻下大丈夫情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您是清楚的。
在我工作第五年末,主管研究室的孙副局长退二线了。局里上下议论纷纷:论才华,论能力,副局长的位置非安吉莫属。不少同事们的眼光对我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孙副局长也神秘地悄悄对我说,我可是竭力推荐你接班的,要努力呀!一个月后,上级的任命下来了,接班的是刚当办公室主任一年的李主任。不少同事为我鸣不平:李主任除了会溜须拍马上货送钱,还会啥?孙副局长责问我咋努力来,我说工作上尽心尽责,生活上谨小慎微。他惋惜道,等于你没努力,大好机会错过了。我明白孙副局长“努力”的意思,也清楚社会上流行的“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口头禅。我却耻于那样做,“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叫我不得尽欢颜!”
没当上副局长,我无所谓,但一帆风顺的生活却由此逆转了。渐渐地,我发现原来仰视我的同事们开始平视我了。偶尔碰到孙副局长,他总是“嗯嗯啊啊”,也不再给我说什么话了,大概是嫌我烂泥扶不上墙。原来那些为我打抱不平的同事们也慢慢疏远了我,团结到新官李副局长周围。
又过了五年,局里又一名副局长退居二线。尽管我的工作依旧出色,为人处世仍得体合礼,还是重点副局长后备人选,但关注的人已不太多了,一是年龄上失去优势,二是宁折不弯的性格没有任何改变。结果这次获提拔的是比我还大四岁的赵科长。听说赵科长的表哥和年前上任的市委副书记是同学。
这次又没当上官,我仍抱着惯看秋月春风的态度,但其严重后果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发现很多同事都开始俯视我了。对需与研究室配合的工作爱答不理,最多也就是支差应付,研究室的工作出现了下滑。一次,我在小饭店吃饭,偷听到隔壁几个同事在窃窃私语。这个说,安吉这小子学历高,能力强,就是当官不行;那个说,他是一根筋,现在都啥年月了,还坚持什么可笑的做人准则,这辈子也不会有啥出息了……,我嗤之以鼻。
我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接送儿子上下学,常听到小家伙说,他同学谁的爸爸是官,上下学都是小车司机接送;还说他同学谁光压岁钱就有几万。有一次小家伙用稚嫩的童音问我:“爸爸,爸爸,你啥时才能当官呢?”我哑然。
每到周末,我总要抽空回老家看望父母。他们也经常说,咱村谁当局长了,整天小车来小车往的;谁当书记了,他爸过生日,送礼的人排成队,云云。言语间多露出几分羡慕。我听烦了,一个月才回去一次,他们又说我不孝。我只好坚持每周去听他们唠叨一次,还经常碰到亲戚陪着唠叨,无非都是旁敲侧击,叫我赶紧想法儿当官。
特别是近两年,年届不惑的我有了最怕的事,就是下班回家。不是妻子不温柔贤淑,也不是衣食住行对我苛刻,只是她同父母一样的唠叨让我无处躲避。今天给我说,谁的丈夫又提拔了,长了几级工资,弄了一套便宜房;明天说谁的丈夫给小姨子安排个好工作;后天又劝我能不能不要那么好面子,咱也活动活动,再不提拔就超龄了……。对于她的唠叨,我一般装聋作哑,不予理睬。说多了,我就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想而知,生气、吵架自然成了家常便饭。
生活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过来了。老师您知道,幸亏我哲学学得好,国学基础好,早就看淡了生死得失、功名利禄,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能吃、能睡,不然也早得抑郁症了。但是,这种生活绝不是我想过的生活。工作单位、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笼罩着同样的阴影,我无处遁逃。早厌倦了,现在我真想回归彼岸。我清楚这样做对党对国是不忠,对父母是不孝,对妻儿是不仁,对亲友是不义,更对不起您对我的精心培养。老师,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安吉来信的字里行间,说明他啥道理都懂。我却困惑了,我清楚给他讲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也清楚,当前像安吉一样困惑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人们常说,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道德良知的中流砥柱。尽管不能解决安吉的困惑,我总该为社会说点儿什么吧!哪怕声若蚊蝇。(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据报道,我国每年有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我一直认为,大学生不想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只想当公务员,对国家绝不是什么幸事。却苦于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直到最近才发现,19世纪中叶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儿认为,如果一国中所有有才华和有能力的人都被吸纳到官僚系统里面,公民的自由就会受到更大的威胁。
一般而言,小公务员凭能力可以混成中层干部,想进领导班子可就难了。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人的单位,领导班子才有几个人?公务员尽管外表光鲜,人前多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但内心深处有几人不为进步整日价忧心忡忡?特别是那些一门心思往上爬的小公务员,他们更是寝食难安、备受煎熬,甚是可怜,乃至悲惨。由此我仿佛看到了鲁迅先生在《淮风月谈﹒爬与撞》中描写的场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人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
让我接着鲁迅先生的话呐喊几声吧!小公务员们,别往上爬了,站起来走路吧!小公务员的父母、妻儿、亲友们,别逼着你们的亲人往上爬了,让他们歇歇吧!
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北京人在纽约》里那几句关于爱和恨的精典台词……
篇三:麻雀的困惑
落地玻璃门在阳光下反射着金灿灿的刺目的光芒。地面瓷砖光滑若镜。风中飘荡着音乐和广告语,以铿铿锵锵的节奏入侵着疲惫甚至懈怠的耳膜。——这是城市的一隅。麻雀出场了。它们的出场在我的不经意间。不过一只麻雀尔,何能激灵我瞌睡的神经?
我用眼角余光扫它一下,继续闭目养神。随之想到孔雀,同样是鸟,褪掉外套都是裸鸟,一字之差,做鸟的境遇就大不一样。如果面前落下的是孔雀,我势必睡意全无一阵狂喜惊呼。想这麻雀,一生劳碌,终生变不成孔雀,变成凤凰更是痴人说梦,不免有点唏嘘。
麻雀有过变成凤凰的想法?
麻雀自有麻雀的快乐,孔雀自有孔雀的烦恼,凤凰自有凤凰的忧虑。
忽然感觉我也是只麻雀。
我搜遍脑海和百度,除了郭沫若应和政治风云作打油诗骂麻雀为“混蛋鸟”,竟没找到一阙为麻雀赋的诗词。一个词语无须百度:门可罗雀。换一个强词夺理的角度,一看就是个挨扁的词!可怜了这麻雀,站个位置也有限制。那朱门豪舍店铺的,是你落脚的地吗?!
麻雀须懂得察风之颜观雨之色,这是生存之道。都与人类朝夕相处,可毕竟不是燕子不是喜鹊啊!
先看人家燕子:“庭前双飞燕,颉颃舞春风”。“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自古至今,卷卷宗宗,吟燕诵燕的妙诗绝句俯拾皆是。燕子、玄鸟、春燕、乳燕......仅人们冠其唯美的名儿就一大堆!再看人家喜鹊,梅枝上一站就梅枝俏,绽放两朵欢天喜地的词:喜鹊登枝、喜上眉梢。
揭人不揭短,戳人不戳软,可有时,事实真地无情到忽略人的情感感受。真相是:如果麻雀寄居了燕子的旧巢,归回的燕子驱赶不走它们,就衔泥把麻雀封死在窝里。
我不知落在面前的麻雀来自哪里,但我骨子里认定它就是土生土长的来自乡村田野的鸟。看它全身土黄色,偶掺杂些腐叶的黑,象极了田间的泥土。我脑海里突然浮出个病句:麻雀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在锃亮光滑的瓷砖上蹦跳的麻雀,它住在哪里?它象漂泊在城市里的某个人,脚上沾满泥巴,衣着尚带泥土的气息。
越来越多的庄稼地被有钱人买断,越来越多的农民惶惶不安,麻雀的觅食空间也越来越窄,越来越少。想起我与发小的通话。他说,你要赞美故乡啊,往后可有好题材下笔了。我们正在搞土地扭转,这几个村要合并到X村去,建一个城市一样漂亮的居民小区。腾出XX亩耕地来,一X国大老板要买断建葡萄基地呢......
我仿佛看到他踌躇满志眉飞色舞的样子。而我,握着电话沉默了,眼底悄悄洇起水雾......不知父老乡亲们或单纯或复杂的情感波动,我敢肯定的是,我发小很高兴。他热血沸腾信心百倍地来参与这件政事,他是“行政长官”。
失了土地,住进楼房,我的父老乡亲,到底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农村和城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户籍档案也给不了全面地诠释,生存方式也无法明确地注解,象一个个村庄坐标的迷失,辩不清经纬线,举目茫然。
我看见找不到谷子地的麻雀,成群飞进了城市,落在城市的繁华喧嚣里。它们在车水马龙间小心翼翼地觅食,在高楼大厦的瓦缝间栖身。高楼大厦的瓦缝在高处,风高不胜寒。麻雀们是否怀念乡村朝阳的屋檐和那淡淡的青草味,无人知晓。
我好象是城里人,我似乎具有沾沾自喜的优越性,所以我不能切肤地读懂麻雀的心事。更何况,我高傲冷漠的眼光不能对接它们暗淡迷茫的眼神。
“我从城市路过,只想寻找一个小小的窝。哪怕有一根电杆子让我落脚,我也感到很美好。我不坚强的外壳,拼命抵抗袭来的夜幕。多少麦子才算收获,我是比一分钱还小的角色”。
旭日阳刚的歌声总让人心生颤栗,词作者就是二人组合之一王旭,他挥着两只粗糙的大手,象只来自庄稼地里漂泊在城市的麻雀。歌声从他们灵魂深处汩汩而来,那一刻,无数计的麻雀闻歌泪盈,燕子为之动容。
居电线杆子的麻雀是智慧有远见的麻雀。电线杆是公共设施,相对于民房,稳定性强许多。我的确见过一家麻雀,它们把窝安在路灯罩里。地处偏远,灯是坏的,光线微弱得如同萤火虫。这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可这恰恰是麻雀得以安居的有利条件。好地段的路灯,麻雀是住不安妥的。
他出生于农村,户口在农村,农村有耕地,他在城里买房安家做事业。小日子过得比城里人舒服。他问我:那我是不是城市人?她户口在农村,但她没土地,她一直生活在城里,她问我:难道我是农村人?——-我无法回答,如同无法定位一只麻雀......
我能回答的是,农村的年轻人纷纷进城,以不同的生存方式,把根拼命地往钢筋混凝土里扎。农村逐渐老龄化,象个垂暮之年的老人,身躯越来越缩水,渐失了青春活力,淡弱了村庄的延续。
若干年后,我会象只迷失方向的麻雀盘旋在曾经的经纬线上,庄稼地呢?村庄呢?叽叽喳喳的鸣声,秋叶一样寂寞地飘在风中。
篇四:种粮的困惑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小麦产量可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年份,我种了六亩地,打了四千多斤麦子呢!”坐在村头大场中人堆里的老郑高兴地说。
“费劲八劳的种麦子,辛辛苦苦一年,你把所收的麦子全部卖了,也不过就四千多元,你全家人忙活一年,还不如我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钱多,人家现在都没有人愿意种麦子了!”坐在他斜对面的小刚不屑一顾地说。
听见小刚这么说,老郑一下子无语了,刚才还跳荡在脸上的喜悦之情被这盆凉水泼得踪影全无。在本庄里,论种粮,他数第一,每年的粮食单产数他最高,可说起钱,就成了他的短腿。他沉默了半响,低低地说:“种庄稼不能算经济帐啊,钱再多,如果没有粮食,你吃什么啊?”
“市场经济,你不拿钱衡量再拿啥衡量啊?只要有钱了,怕什么,咱才不管它粮食丰欠呢!”小刚坚定地说。
“我在想,这农民不种粮还叫啥农民呢?‘只要有钱,不种地无所谓’这个观念一户二户这么想无所谓,一个村一个乡这么想也无所谓,一个县一个市这么想恐怕问题也不大,但所有的人都这么想,那麻烦不就大了?”
“怕什么,咱们这边没粮了可以从外地调运,外地没有了可以从外国进口!”刚从初中毕业的小龙也跟着发表起了意见。
“你黄毛小子经过冬吗经过春,知道个啥,你没经过五八年,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等到真的遇到年景不好没粮食了,你狗娃的肚肚饿扁了,恐怕嚷嚷的比谁都厉害。”七十多岁的任大爷一边笑咪咪地摸着胡子,一边说。
“别翻那老黄历,时代不同了,现在怎么能跟过去比呢?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谁还为吃饭发愁,你这不是人家所说的‘杞人忧天’吗?”小龙嘟着嘴说。
“是啊,最近几十年来,年年都风调雨顺,农民家家户户都粮满囤,粮食的问题似乎已没有多少人关心了,政府都在鼓励咱们改种果树、药材、蔬菜等收入高的作物,小麦播种面积比过去少多了。想想这也没错,粮食固然重要,但每斤也就只卖一元钱,从收入的角度看种粮实在划不来啊!”人称百事通的李保全也加入到他们议论的行列。
“市场经济的确好,人们的生活都富裕了,家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是,日子过得越好,人越安逸越懒了,过去家家都养猪养牛养鸡,农村到处能看到活蹦乱跳的牛娃猪娃,人们把山地的角角落落都种的到到的,可现在呢,虽说钱是有了,可十户八户下来,养猪养牛的最多一两户,养鸡的也寥寥无几,都指望着打工挣钱去买,你看看,现在山地除过退耕还林的,一大部分已经撂荒了,现在农民手中的实物财富已越来越少了!”在乡镇工作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回家的老扬忧虑地说。
一旁边七嘴八舌的人一时没了语言,他们也明显觉得老杨说的没错,的确,现在农村养牛养猪的人已经很少,人们都嫌破烦,就平时吃的鸡蛋,也到商店里去买。
“等我们这些老年人相继去世了,看谁来给你们种粮食,你们不是说你们有钱吗?到时候你们去吃钱吧!”老郑似乎找回了失落的优势。
听着他们的辩论,看着这一堆堆丰收的麦子,我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似乎说的都有理。
“囤里有粮,心里不慌”,这是农村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农民种粮,原本天经地义,不为嫌钱,只是生存的本能,但如果农民自己也认为我们可以不种粮了,如此的观念蔓延开来,那问题恐怕就严重了。
记得有个寓言故事:说某地遭了水灾,两个逃生的人爬上高处的两棵大树,由于走得匆忙,张三背了一袋金币,李四背了一袋干粮。洪水久久不能退去,第一天,张三用一个金币买李四一个干粮,李四不肯;第三天,张三用十个金币买李四一个干粮,李四仍不肯;第五天,张三愿用一袋金币换李四一个干粮,李四还不肯。七八天后,洪水退去,李四得以生还,而张三早已淹死在洪水中。
不知道这个寓言故事中的情境是否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粮食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人的生命与它息息相关,它真正的价值是不能简单的用金钱来衡量的。
本文由散文网用户整理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